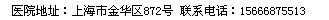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胃反酸 > 治疗方法 > 飘零的莜麦花
飘零的莜麦花
人的一生在记忆的长河里竟是那样短暂,象夜空划过的流星匆匆而过,可有些经历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九六八,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青年如此特殊的群体,他们的青春是在最艰苦的农村牧区兵团经受水与火的洗礼,无由的磨难,撕心裂肺的彷徨,惊心动魄的生存故事,书写了人类历史浓重的一笔,让我们记住他她们。
飘零的莜麦花
——踏上寻访故乡的车轮(上)
图/文雷时之
一
汽车在大青山公路上颠簸着,窗外的山景穿成串儿,我好象睡着了,似乎还打起了鼻鼾。坐在后排的赵瑜一本正经地说:“老雷,你的呼噜声可是不小呀!”,“是吗?”我诡异地揉了揉眼睛。
人上了年纪毛病增多,记得插队那年,我还是一个道地的小鲜肉,白的确良衬衫,灰蓝布短裤,土黄色的塑料凉鞋还算合脚,衬着可爱天真无邪的脸蛋儿,好精神的小伙儿,一路唱着老人家的红歌飞跃过大青山。中途下起了毛毛雨,同学们的歌声反而嘹亮起来,我迎着细细雨丝伸出了舌头,好凉快呀!,那精神头儿,怎么,今天困得睁不开眼了?哎……这岁月。
内蒙古大青山
当年我们这些只会啃书本的京娃娃为了老人家发动的文化革命买单,糊里糊涂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旗子,背井离乡公里,来到了祖国最边远的地方插队落后。中学生的我们会什么呢,读书写字做早操,跟着印尼华侨英文老师念:“Twinkle,Twinkle,littlestar!”。
年9月2日
突然有一天闹革命了,校园成了屠场,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打砸抢的“红卫兵”,红扑扑的书生脸上拧起了恶狠狠的麻花,书记校长老师挂上黑牌做“喷气式”,当年教书育人的楷模转眼成了“阶下囚”,白纸臭墨汁的大字报贴得校园哪哪都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搞不懂。抄写大字报,画牛鬼蛇神,这点我是专长,毕竟在少年之家学过美术,抡几张刘少奇漫画像富富有余,不就是大鼻子上多戳几个点呗,哈哈哈……惹得大家莫名其妙一笑。这些半大小子闺女来武川作甚?该不是到农村闹革命吧?哈,哪有这好事!
那个年代风华正茂的作者
“你又睡着了吧!”,坐在旁边的尹平嘟囔着,“呵呵!”我象是傻笑着从记忆中走了出来。猛一抬头,怎么?都到武川了?“没少做梦吧?一路打着呼噜,你就差说梦话了!”,坐在前面的金刚诙谐地提醒道。是呀,昨天晚上睡在呼和浩特市,旅店里居然有蚊子,咬的一夜没睡好,怨不得今天这么困哪!眼睛得用草棍儿支着才能打开。
年回乡在聚金山村见到老乡许六
这一车人都是当年武川东红胜公社的知识青年:东兴业堂的金刚,尹平,南泉子的赵瑜,我和豆包落脚在聚金山,40多年后重新踏上寻访第二故乡的路。山还是那座山,小草晃晃悠悠,一连四五十载,村里变成什么样了?乡亲们还好吗?
俄罗斯伟大画家列宾的油画《伊凡雷帝弑子》
其实,我10年前回来过一趟,村里人老辈儿的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也记不得是贵金子还是栓小子指着炕上的老父亲说:“瞧那老不死的,就圪蹴在炕上呢!”,我心中一愣,急忙爬上炕和老人家握了握手。风烛残年的老汉浑身在抖,大滴的眼泪漫过干扁屈黑的面颊,暗灰色的眼珠痴呆呆地望着我,那样无助,甚至是绝望,使我不禁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油画《伊凡雷帝弑子》,岁月呀风霜刀剑,更何况这阴山北麓恶劣的气候,人生真是一场梦,春暖桃李花开日,秋寒梧桐落叶时,落叶要寻根。
二
内蒙古自治区的武川可是个老物件儿,距今年前的北魏在都城以北的边境设置了6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用以抗击草原霸主柔然族的入侵,武川镇中,都府平城(今大同)当然把武川作为一个军事要冲来拱卫都城。千百年来胡汉杂糅,金戈铁马,枭雄辈出,北周皇帝宇文泰,隋朝文帝杨坚,花花太岁隋炀帝,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都是生于长于武川,至于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数不胜数,仔细算算好一个“了得”二字能够圆说。
看来我们的老人家是用心了,把这些文化革命的年青火种播撒到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接受水与火的洗礼,莫非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他哪知道京娃娃看到的武川,建国近20年仍然是一座黄土没脚素面朝天落后的北方边城,即看不到隋代宫阙庙宇迤逦的屋影,也领略不到大唐盛世铁马金戈的雄风,更没有建设一个新中国改天换地的气象,倒是飘零的莜麦花翎漫山遍野向新来的小主人露出了粉绿色的笑容。
丰收在望的莜麦
汽车开进环城公路,车里知青兴奋起来,一个个指手画脚,40多年了,真是变了。过去站在山梁上手搭凉棚瞭一瞭,武川县城就象是一片莜面窝窝山药蛋,一出水的土胚房沿着大黑河支流河床边的缓坡平铺直叙,满眼褪色发白的泥屋顶象未炸熟的油糕带着几分夹生气。城中心唯一的一条大街还是土路,晴天满身土,雨天一身泥。街两旁有些像样的砖瓦房,自然是县政府大院。电影院是当时最牛逼的建筑,大小两层楼房,还设置了提供演出的礼堂。
那个年代样板戏《红灯记》海报
记得当年武川县举办知识青年乌兰牧骑汇演,我,麻线,今天,欣久,朱定清一帮人代表东红胜公社PK另几只公社代表队,就是在电影院的舞台举办的。当时拿手的演出剧目是《红灯记》,那个年代8大样板戏一统天下,说梦话都要喊出“我有一颗明亮的心”。朱今天饰李玉和高大威猛,朱定清饰李铁梅,兰花指顾盼巧兮,欣久一派李奶奶家风的威严,我,惨了点,整个饰一个侯献璞:卖木梳的暗号联络人,台词就一句“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说完就打发下台了。
作者在武川县城
武川县城
可侯献璞那一身行头我可是用心准备了,潲色咔叽布的风衣还是父亲当年留学美国的行装,抄家时红卫兵嫌旧,没给抄走,鸭舌帽是老麻借给我的,打扮好照照镜子,嘿!的确象个特务样。最后一个节目是对口词,麻线还没报幕完我就紧跟着屁股撵上台,只听麻线回头一声:“下去!没轮到你呢!”,我臊得满脸通红,头皮冒出冷汗,灰溜溜走下台。一晃40多年,俊男靓女已生白发,人间不再是四月天。
冬天的武川县城
大家七嘴八舌,指指点点,不经意间汽车已开到可镇中心。武川县所在地原名叫“可可以力更”镇,蒙古语:青色的山崖,大青山麓绵延的丘陵青山绿野,碧草如茵,黄艳艳的油菜花,粉绿色的莜麦菱迎风招展,焦黄的麦穗,笑眼的荞麦,举着胖脸的向日葵也加进了这多彩的大军,预示着武川又迎来一个丰收年。
武川秋景
今年的收成应该是不错,雨水多,山洼子河滩下居然聚成了小湖,明晃晃的,像杨贵妃亮闪闪的梳妆镜,毕竟还是靠天吃饭,连片的庄稼地随着山坡起伏,绿的一片黄的连绵粉的成串儿,好一副山峦织锦,五彩后山。看着熙来攘往武川的新住民,看着宽展的公路簇新的楼宇现代化的街市,武川真的要变了。
远处的河滩
三
“百灵鸟儿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歌唱……”,望着车窗外满坡的油菜花,莜麦菱,向日葵,簇拥着的麦穗我不禁小声哼起了老电影《草原上人们》的插曲,曲调委婉悠扬,跳动的音符象仙人无形的玉指轻轻梳理着后山这七彩的山坡。初秋的武川确实很美,不再是盛夏白毛烈日,如果雨水好,青山吐翠,万亩黄金。
麦子熟了
我清晰记得当年知识青年的专车一到东红胜公社,同学们象炸了窝的麻雀扑向路边高高的莜麦地,北京城里的京娃娃哪见过这么多的庄稼,短裤花裙,细嫩的胳膊腿被麦芒刺扎的生疼,但大家的兴致不减。突然麦子地里窜出几只麻雀从头顶上掠过,悬浮在半空中,随着煽动的翅膀一串优美的音符撒向万里无云的蓝天。
百灵鸟
穿单衫子老农民笑呵呵告诉我:“那叫百灵鸟儿,百鸟之王,叫声可好听了!”。“真的吗?”噢!我想起来了,外公最喜欢百灵鸟,插队前头一天的晚上还嘱咐过我内蒙出产百灵。以后插队的几年,每到拔麦子的时节,不管营生多么苦重,我都会哼着百灵鸟的歌儿仔细查看麦子地里有没有小百灵的身影。
功夫不辜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逮住了一窝小百灵,刚破壳的雏鸟嗷嗷待哺,四张乳毛小嘴象张开的黄花菜稚嫩鹅黄,我学着外公喂鸟食的方法用鸡蛋黄掺些白面调制饲料,耐心往那大张的小鸟嘴里喂食,叽叽喳喳,好可爱的小生命。四只小百灵健健康康地满月啦!正好聚金山东队的菲拉要回北京探亲,我把他当做头等大事向菲拉求援,好心的菲拉呵护有加,真的把小百灵们平平安安送到我外公的手中。
记忆中的外公
外公是清朝的举人,爱养鸟,米丘林白胡须下一身藏蓝长袍,文化革命前我家堂屋里挂了一串鸟笼,什么白玉呀,画眉呀,子子红蓝点颏呀,不过外公最喜欢百灵鸟。清晨,外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鸟笼上的蓝布罩揭开,百灵鸟抖了抖身上的羽毛,清了清嗓门,脖子一扬,几串美妙的叫声萦绕在厅堂,清脆婉转和着早晨第一缕阳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年破四旧,可怜的鸟儿都被红卫兵当作牛鬼蛇神抓走了,为此外公几个月没说话,躺在藤椅上痴呆呆地望着窗外,一把银白色的胡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这回可随了他老人家的愿,老态龙钟的脸上又泛起了红光,谢谢好人菲拉。
网上图片
应金刚的要求汽车在路边停下,面对着百亩盛开的油菜花,大家张开了双臂,恨不得把这漫山的美景尽揽怀中。我们举起相机要照,“注意取景和白平衡!”豆包甩过来一句话,全体愕然!豆包现在是老年摄影班的高材生,对怎么照相专业术语一套一套,看来我这学了一辈子美术的人也要与时俱进了!
留个纪念吧
东红胜公社到了,司机把车停好,5个知青一块儿下来找感觉,还是当年的东红胜吗?不象,确实不象了,街道商铺多了,可是村子变小了,公社的大院在哪呢?一时茫然。记得那年我们这一卡车京娃娃刚拉到公社,就被各村跑来的社员们团团围住,头一次猫见北京的闺女后生,如同见了西洋景,簇拥着大家挤进公社大院。
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堆着笑脸盛致欢迎词,又是革命小将,又是红卫兵,通篇溢美之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郝书记的最后一句话语铿锵,脸上的肌肉随着激昂的声调在聚拢跳动。开饭啦!老乡们端起一碗碗山药烩菜举到我们面前,好巨大的糙碗,冒着蒸腾的热气,我头一次夹起一寸见方的肉块儿往嘴里送,撑得腮帮子鼓鼓的。每位同学还发两个半斤重的白面馒头,象一对儿小枕头搂抱在怀中,你别说,白灵灵的馒头真松软,散发着发酵过头的酸香,武川的名菜:土豆羊肉烩菜,这一刻我们记住了。
饭还没吃完,各个生产队派出迎接知青的“专车”已在公社院墙外一字码开,嚯!威风呀!所谓专车就是三匹马拉的两个木轱辘大车,选派的车夫大部分是各村的年青后生,各个手握着拴有红绳的鞭杆儿,颇有点儿将帅派头,几十匹马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雾气,脖子上的马鬃如同抖动的旌旗飘洒飞舞,我忽然想起了电影《宋景诗》里黑旗军的马队,趾高气扬,有几匹马鬃上还用红头绳扎成了小辫儿,威风凛凛。城里的娃子一见这阵势,全都围拢过来,伸伸手探探头,左瞅瞅右看看,很快就按事先预备好的名单坐上了不同生产小队的接风马车。
作者在东红胜公社
聚金山西队指派的是队长武长命和栓小子,南泉子接知青的车倌二福善胡二仁听说京城的女娃娃长得白净又有知识,舌头上下浸满了含水(口水),暗地里早早打起了“坏”主意,怨不得来公社的路上就满嘴念叨着“接新媳妇喽!接新媳妇喽!”,马车一到大院门口,俩人眼珠子滴溜溜转,偷悄悄地捞色(寻找)着漂亮的女知青,果然,功夫不白下,没出二年双双抱得美人归。
武川莜面饸络
汽车要发动了,尹平提出想尝尝当地的混糖“月饼”,我也特别喜欢吃,几十年了,念叨起来哈喇子都快流出来。胡麻油烤出的贝子和内地月饼就是两种感觉,一口下去强烈独特的麻油香味绕着舌根走,有些飘飘欲醉,供销社小卖部的货架上还真放着几包,我们付了款抱起月饼就钻进了车,满嘴的幸福带动了寻访故乡的车轮。
四
下了公社的南坡聚金山已可极目远眺,路两边的麦子莜麦丰收在望,成片的麦田象黄金锦带横绵在起伏的山丘,一眼甚至望不到边。摇头摆尾的麦穗故意挑逗我的神经,针尖似的麦芒划到胳膊上留下一道道白印。
想起当年拔地季节真象过鬼门关,为了抢收粮食颗粒归仓社员们起早贪黑,我们这些知青娃子手脚比不了当地的老农民,不得不凌晨4点打着手电筒认垅,笨鸟先飞呗。一头扎进麦垅里你就别想抬头,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拔呀拔呀,飞起的土块连炮黄尘,遮天蔽日,膝盖下绑的布片七零八落,浑身象个刚出土的兵马俑,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眉毛胡子挂满黄土,虽然带着自制的拔麦子手套,两天下来双手早已勒满了血泡,人也快散了架。
远眺聚金山
隔壁的老娘娘看着心疼,“呀呀!这成什啦!满手血巴子!”,她划了支起灯子(火柴)用火烧了根针,细心地给我挑开血泡,敷了些红药水。本想歇一天,不行,生产队拧得紧,连拉带拽又把我们扔进了无边无沿的麦海中。旁边的老乡不知从哪个道叉叉(裤子兜)掏出个海红子(沙果)扔给我,顾不上果皮沾满的泥土,我一口咬下去,清凉酸甜的汁液流了一嘴,我跪在麦地上,大张着嘴,任凭着果汁在口腔里翻动,真舍不得咽下去,仰望着蓝天,实在不愿意这难得短暂的幸福匆匆离去。
麦收时节
这些日子我和同屋的知青小会实在累得直不起腰,好好的后生才几天脸上晒出了黑疙楞,满嘴火泡,胳膊腿象医用的骷髅骨架,滴了当啷。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自打插队起他老人家的巨作一直压在枕头底下支撑我生存的信心,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对美好的憧憬,都是从被砸抄的学校图书馆里收集起来的。
作者和队里的知青
有一天半夜出工的吆喝声又响了,我探头窗外,还是满天星斗呀,“怎么?今天吆喝的也太早了”,我们实在是爬不起来,只好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生产队长武长命拐着腿边吆喝边挨家挨户“抓人”,我俩趴在土炕上大气不敢出,望着“将军不下马”(一种门锁的别称)队长还以为我们早已出工下地了,一瘸一拐消失在夜色中,我差点笑喷出声来。
年回到村里看望老乡
聚金山村边是一大片河滩,每到雨季好美哟!满地打伞的没打伞蘑菇争相从泥土中探出头,裸露白崭的好肌肤,象西施的迷人的酥胸还是贵妃性感的身段,还有赵飞燕,你猜?盛开的马莲花举着淡紫色喇叭状花瓣不住地点头,好像有多少小秘密要诉说,只要你舍得蹲下似乎真的听到了这里故往的传说。解放前土匪鄂友山可是这块土地的霸主,听老乡说那些家伙们凶神恶煞,一身白茬子皮袄跃马扬枪,从大青山到百灵庙,好像这方圆几百里都是他们家的自留地,想到那家夜宿不能有二话,甚至搭上姑娘媳妇,这片河滩曾经是土匪们放马的上好草场。
作者在聚金山村前
可不是,河滩的草长得肥美粗壮密密丛丛,深绿色的叶片几乎要渗出汁液来,我在这片河滩上当过马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点道理如今贪官儿们都学会了,哈,这是后话,你懂得。夜黑漆漆的,冷风从耳边剌过,我躲在羊毛雨毡里瑟瑟发抖,赶上暴雨天,雷鸣电闪,豆大的雨珠象断了线的珠帘,噼噼啪啪摔碎在脸上,眼前溅起一层水雾,脚下一汪雨水流成了小河,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望着天边的霹雳火,真有如《庞贝的末日》,这无垠的黑暗,一个人的世界好惊恐。
美丽的河滩
要是晴朗的夜晚,河滩就又是另一番景象,弯弯的明月挂在半空中,象镰刀还是姑娘的芳唇?悠悠地向你抛出飞吻。马儿低头吃着饱含露珠的青草,发出“嚓嚓嚓”的声响,四野一片寂静,银色的月光轻抚着马群光亮的脊背,移动着,变换着身影,我忍不住唱起了《草原之夜》:“想-给-远-方的-姑娘-捎-封-信-去……耶……,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递……”。是呀,我们这些男知青身无分文,一身破衣拉洒的光棍儿,哪个姑娘会看上我呀,望着月光中枳箕晃动着孤零零的黑影儿,眼泪流向心中。
赵瑜提议该下车了,眼看就到村口,一把刹车大家从座位上倾起,接着就是起了咔嚓一通照,毕竟是第二故乡,人不亲水还亲,何况老乡楞眼瞭盼着呢!最有发言权还数豆包,当年披红挂绿走过一遭,“站好,站好!”豆包拿出职业摄影师的架势命令道,我们几个及时遵命站成一排,一阵微风飘过头顶,乡土的味道迎面扑鼻浓浓的,我不禁又胡思乱想。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奇怪,为什么是故乡呢?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本可以象现在的年青人那样自主选择职业,挑选未来,甚至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我们可以携手浪漫的姑娘去喝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合上书本憧憬似锦的前程,我们可以……?可是我们却被忽悠到面前的“故乡”修理地球,有什么原罪说吗?我们才刚刚走出校门呀!这两天看基督教书籍多了忽然想到,脑勺后有只鸟从头顶上窜过,叽喳怪叫声打断了我灰色的思路。
五
汽车终于在聚金山东队村口停下,把我们三个放下,金刚,尹平要回他们当年落户的东兴业堂。炳生子,小老虎和另外几个东队老乡已在村口等候多时。“老啦!你可多胖啦!”“咋不老呢,快50年哟!”大家激动的相互狠命地握住对方的手,就怕彼此从地球上消失,眼眶盈满了泪水。可不是吗!问张三张三没啦!问李四李四早死球的啦!现在出气的真没几个!命运多舛。正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太阳投下的阴影把这一群患难与共的乡亲知青象链条一样紧紧笼络在一起,空气似乎凝固,人生不过百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别离,又是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社员们怎么会不老呢,我们在京城混了几十年如今不也满脸爬满了瓜纹。
老乡在村口迎接
记得刚落户到农村,知识青年简直就是一群血气方刚活蹦乱跳书生气十足的姑娘小伙儿,拿现在时髦的话叫漂亮的萝莉动感小鲜肉,年青,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活跃,如同初生牛犊。当时正赶上内蒙大搞内人党(所谓反党组织),按着上面的旨意地富反坏右都属于怀疑打击对象,我们巨西队的幸子美只因为成分是地主,被这些京娃子折腾的不得安身。我,梦久,徐文明半夜窜到老乡家查夜,当地人有个风俗,因为皮袄,单衫子(内衣)里长虱子,不管男人女人,姑娘媳妇,晚上睡觉都要赤肚子,也就是光着身子呗!光个溜溜,睡得香也不怕虱子咬。这些知青毛小伙在公社革委会的怂恿下,以打击坏人抓流氓抓反革命的名义,每次闯门入户被子一掀,把人家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赤身裸体地问三道四,幸子美不堪忍受如此的侮辱,那年冬天顶着白毛糊糊般的风雪投井自杀了。公社听闻反而对知识青年大为表扬,称赞我们阶级分明立场坚定,可怜的一个活人就这样含冤离开了如此政治动荡的世界。
作者和聚西队的喜权子三蛇子
新人新气象,队里要画主席像正愁没找着画匠,我这北京北海少年之家美术班的高徒自然义不容辞,和下河村的苗力联手承接了这项政治任务,是呀,老乡们都等着哪!早请示晚汇报哟。笔,广告色买来了,没有调色盘怎么办?我住的卢员外土房后面是村里的垃圾堆,里面掺杂不少碎碗碴子。好办,大半个碗碴的调主色,不就是红红黄黄吗!只剩下碗底儿的搁辅色,呵!没半点功夫一套十几个颜色的碗碴调色盘聚齐了,象罗列好的架子鼓。开画,文革小将的红色功夫没白炼,爬上爬下,橙黄打底,赭石描轮廓,再勾上眉眼,活脱脱个老人家像不到一天就完工,刷上三遍清漆,齐活。村里老乡还真当回事,队长带着敲锣打鼓红火了好几天,天都黑了,还有三忠于太深的人举着红宝书对着老人家像没完没了的念叨。
文革大画主席像
不出仨月,刚来的热活气烟消云散,艰苦的知青生活横在眼前。天寒地冻,大家要象社员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一日三餐,知青和老乡一样真的过起了“家家”。自己打井取水,烧火做饭,骑上马到公社去驮粮食,养猪喂羊,抹墙脱丕,走上10里地跑到东红胜供销社打点煤油点灯,套上队里的骡子转磨磨面箩面。收割下的莜麦拿到生产队的火房漂洗晾晒,倒进初稍大铁锅里点火翻炒,弄成半生才能磨面做莜面窝窝,压饸络。队里的骡子不是太老实,拉到磨坊上磨,眼罩戴不好,这牲口会斜眼偷看,踢她打她也不走,好容易走顺了,哪儿没伺候好冷不防踢你一脚,把搓面笸箩打翻在地,白生生的面粉荡了一身,好可惜。
抓住这最美的瞬间
十八九岁的学生,在北京只知道读书写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哪会炒菜做饭,女生梁中安甚至糖盐不分,把好好的一锅山药烩菜放了半瓶子白糖,甜得齁人,李梦久更是把煤油当醋倒在菜锅里,毁了一天的好心情,生活不再是一首浪漫的歌。在学校时老师多次夸口:你们才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红领巾红旗红海洋,低头看看现在的自己,半年下来灰头土脸,衣衫褴褛,两手磨出了和年纪不相仿的老茧血泡,原来,我们是国家的包袱,革命的弃儿,解决就业的出气筒,“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望着村头我亲手绘制的老人家画像和书写的标语,这一大帮知识青年茫然了。
六
屋子里飘出了莜面的蒸香,象寺庙里的香火悄悄从背后袭来,微醺细腻,“晌午了啦!快进家吃个饭!”,老乡热情地拉扯着。一大早的颠簸,肚子还真有点饿,炳生子的媳妇端上了刚出笼屉的莜面饸络,酸菜辣椒子黄瓜丝盐汤好亲切,“怎么没搁蛮茎?”我脱口问了一句。“蛮茎”是一种后山特有的腌酸菜主料,形状个头儿如同芥菜疙瘩,每到秋天武川人用青石板压酸菜缸,第二年开春捞出腌好的蛮茎,酸脆爽口还带着一股与石头沫发酵的乳香味儿,是莜面沾盐汤的绝配。“头年的吃完啦,新的还没下来”炳生子回复道。
搓莜面芋芋
记得我们这群知识青年头一次吃莜面窝窝芋芋就上了瘾,爱吃的不得了,但不会做。隔壁老娘娘手把手教,只见大娘滚水泼好莜面,反复揣到筋道,青石板上擦些素油盘腿坐在炕上,掐块面荠子悠闲地用掌心一推食指一挑,薄如蝉翼莜面窝窝做好了,一排排一笼笼,象饱含菜花蜜的蜂房。我们几个按耐不住上手小试,不知道手笨还是用劲儿过猛,推出来的莜麦卷薄厚长短不一,放在笼子里七歪八斜参差不齐,惨不忍睹,“整个一踩瘪了的马蜂窝”小会调侃道,大家哈哈大笑。
莜面窝窝
笨人有笨办法,当地的光棍儿劝我们别那么麻烦,怎么个不是吃,摸“刨扎子”就行,“刨扎子?”我俩想探个究竟。光棍党来顺捋胳膊挽袖亲手示范,只见他黑区区的胳膊用块莜麦面擦一擦,就开始在手臂上推了起来,事毕推过莜面的地方露出肌肤的白嫩,我不禁喉咙里反上了一股酸水,胃中感到恶心翻腾。不曾想没两天,随着村里农活劳动强度加大,知识青年累得早已无暇品味烹调精耕细作,“摸刨扎子”莜面卷儿已经成为一日三餐果腹的常态,我甚至发现用大腿内侧推莜面更得心应手来得快,原汁原味吗,嘿嘿!
武川白玉山药蛋,极好吃
一年以后,知识青年的生存能力大幅提高,不但工分快追上老乡,各种农活已不在话下,我甚至扮起了屠夫的角色。杀猪是个肥差但又绝对技术活儿,老乡们杀猪还是老传统,四只蹄子一绑钝刀抹脖子,猪疼得嗷嗷叫,五里外的下河村都能听见凄惨的叫声,况且一头猪屠夫恨不得敲走半只:头蹄内脏,猪头槽头肉猪尾巴,算了,我还是自己来吧。从北京买了本农村读物《屠宰指南》,按着书中要求我请开车床的同学罗光燮加工了几把屠宰用的刮刀带到了后山。
网上图片
第二年秋后我俩养的黑猪吃得膘肥体壮,到了宰杀的日子,自己上阵。捆好四蹄,卢小会递来根木棒,我照着大张的猪嘴一捅一撅,顺着黑猪嗓子眼底下的白毛扎进,说时迟霎时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鲜血象冲洗汽车的水枪喷射出来,黑猪来不及嚎叫已撂倒在地。如果是约克夏白猪,嗓子眼底下的白毛比周围猪毛硬,“知识就是力量”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被我拿来向老乡卖弄,“瞭瞭!还是你啊北京知青有本事”,乡亲们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下一步挑开猪后蹄筋,把打气管插入后腿皮下朝猪皮里面打气,边打气边用木棍敲打,猪死一千棍的谚语大概由此得名,便于退毛,不一会儿黑猪涨得圆鼓鼓的,猪毛直立象个巨大的刺猬。我摘下门板架在烧满滚水的大铁锅上,把猪后腿悬挂在房梁顶,半个猪身子斜搭在门板上开水冲浇刮毛,小会死命地拉着风箱,滚水被旺火烧得咕嘟咕嘟作响。“死猪不怕开水烫”,完事后开膛破肚,大卸八块,猪血灌肠,整整忙活了一整天。
宰羊
乡亲们看我如此熟练,“雷一刀”的名声传开了,聚东队,红河槽都有老乡请我操刀,村里宰羊杀牛更是要请我出场,甚至盖房压栈也让我和小会助阵。每次“走穴”我都按屠夫的标准槽头肉一鏇半乍多,猪尾巴连着小半个臀剜下来,哈哈!收获颇丰,生活质量提高不少,又是油糕又是面,半夜柴锅里还炖着牛骨汤,远近的知青闻讯后没有不来沾点荤腥的,望着窗外西瓜大的满月我想起了北京的亲人。(未完待续)
蔬菜饮食有禁忌nbsp蔬菜这个部位不健康慢性胃炎的饮食调理一定要遵循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