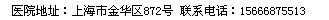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胃反酸 > 相关医院 > 芸香小说水云楼的梦上
芸香小说水云楼的梦上
编者按:水云楼,在江苏泰州溱潼镇的古寿圣寺内,建于明初。清代著名词家蒋鹿潭曾谐黄婉君寄居水云楼,其词集亦沿用楼名。
蒋春霖(~)晚清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曾官至两淮盐大使,遭罢官。一生潦倒,后因情事投水自杀(一说仰药死)。早年工诗,中年毁诗而一意于词,与纳兰性德、项鸿祚有清代三大词人之称,所作《水云楼词》以身遭咸丰年间兵事(太平天国运动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多感伤之音,有”词史“之称。诗作传世仅数十首,称《水云楼烬余稿》。
芸香·小说
水云楼的梦
◎沈尘色
一
这些日子以来,蒋春霖越来越觉得头痛了。有时,索性便是感到头痛欲裂。右手食指死死的摁在鼻梁骨上,似乎能够减轻一些痛苦,可这样的痛苦始终都存在着。
“婉君,”蒋春霖呻吟着,“你帮我揉揉。”
婉君便将蒋春霖的右手拿过一边,用自己的右手在他的鼻梁上轻轻揉动。
“婉君。”蒋春霖低低的呼唤了一声,翕动鼻翼,贪婪地嗅着从婉君手掌上传来的幽幽馨香。
“婉君,你不要离开我。”蒋春霖用一种奇特的声音仿佛是在哀求着。
“不会。”婉君很淡漠地回答道。
这样的淡漠使得蒋春霖有些难受:“我真的已经老了。……婉君,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婉君,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没有。”婉君还是那么淡漠地说道,“我要做饭去了,爷。”
蒋春霖迅速地抓住婉君的手,低叫道:“婉君……”
婉君说:“真的要做饭去了,爷。”轻轻地抽出手来。
望着婉君离去的背影,蒋春霖忽就觉得心头一阵阵的酸涩与哀伤。
婉君,真的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蒋春霖是在前年遇见黄婉君的。
一生漂泊伶仃凄苦的蒋春霖在遇见黄婉君以后忽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调寄卜算子
杜小舫说:“鹿潭翁怎么这般凄苦?”很快的,杜小舫就打听到,蒋春霖竟是为情所困。杜小舫笑笑,不动声色的,将歌女黄婉君就买了下来,转送给蒋春霖。蒋春霖至今犹记得杜小舫将婉君送进门时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杜小舫说:“鹿潭翁,你身边确实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了。”
“我……”
“婉君读过你的水云楼词。呵呵,‘小红低唱我吹箫’,当年的姜白石有可人的小红,现在,我们的鹿潭翁有可人的婉君啊。”
蒋春霖老脸微红,却怎么也掩不住心头的喜悦。当他转头去看从轿子里缓缓出来的婉君时,他的心就越发地跳得厉害了。
婉君的脸色却是淡淡的,看不出丝毫的表情。
“婉君,婉君。”蒋春霖浑没在意,只是抑制不住地低唤着婉君的名字,这个名字,仿佛是他一生的希冀与幸福似的。这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的体验,没想到到了晚年,竟突如其来。
“爷。”婉君福了福。
婉君的声音是那么的柔和,像水,是的,像水,似乎就要将蒋春霖给化了。这么多年以来,动乱不堪,蒋春霖四海飘零,到今天,忽就有了家的感觉。是温馨的家。是叫人满心牵挂的家。就因为有了这个叫黄婉君的女子。一个年轻的女子,生生的,就在眼前。
蒋春霖将婉君带回了溱潼。
婉君始终都是那么淡淡的,似水,却是那种不起任何波澜的水。起先,蒋春霖没有在意,后来,见婉君的脸上始终没有什么笑意,蒋春霖也就有了些隐隐的不安。
但婉君毕竟始终陪在他的身边,给他做饭,给他缝补,每逢有新词写出,婉君还会清唱一曲。蒋春霖虽做过两淮盐大使--这分明是个肥缺--可他不谙官场,又不善于治生,歌楼酒馆,随手散尽,到罢官归里,早已是两袖空空。杜小舫尽朋友之谊,将婉君赎出,转赠于他,可日常终究应有些用度。蒋春霖这时的捉襟见肘,使他对婉君就更加的不安了。
二
婉君艰难地将脚步挪动到厨房的时候,忍不住就想大哭一场。
婉君忽然发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再也无法开心。幼时也曾有过灿烂的童年,也曾有过美丽的梦,可随着世事的变迁,竟迅速地沦为歌女。或许,这就是命运?歌女生涯原是梦。在梦里,婉君便时常想起前朝的“秦淮八艳”:一样的歌女,却能青史留名,便是到现在,又有谁不赞一声“奇女子”?于是,当杜小舫替她赎身的时候,她稍稍犹豫一下,也就应允了。婉君说:“蒋先生是不是太老了?”杜小舫笑:“比诸当日的河东君与钱牧斋又如何?鹿潭翁一代词宗,决不会辱没了姑娘你。”婉君原先就读过、唱过蒋春霖的词,杜小舫这一说,婉君便点头。更何况,以她的身份,本来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将来。
一袭小轿,婉君就被杜小舫当作礼物送给了蒋春霖。
蒋春霖是爱着婉君的。这,婉君当然也知道。可婉君只要一想到这个说着绵绵情话的词人已经五十岁了,忍不住就有想哭的感觉。有时,婉君简直就怀疑,那么多优美的词句,怎么会出自眼前这个穷愁枯瘦的老人的笔下。
婉君犹自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日随蒋春霖回溱潼,经过黄桥的时候,泛舟水上,蒋春霖随意谱写的一阕《琵琶仙》:
天际归舟,悔轻与、故国梅花为约。归雁啼入空候,沙洲共飘泊。寒未减、东风又急,问谁管、沈腰愁削?一舸青琴,乘涛载雪,聊共斟酌。更休怨、伤别伤春,怕垂老心情渐非昨。弹指十年幽恨,损萧娘眉萼。今夜冷、蓬窗倦倚,为月明、强起梳掠。怎奈银甲秋声,暗回清角。
蒋春霖写罢,便令婉君歌唱。当日,婉君一边唱着新词,一边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由潸然泪下:南京城的火光与鲜血,在眼前就再一次地出现。
蒋春霖安慰她说:“现在,一切都已过去了。”
婉君幽幽地叹息。
在从南京城逃出的时候,与家人失散,想来,她的家人在那场屠杀中早已不复存在了吧?而她,孤零零的,迅速地就成为一个歌女。因为她要生存。幼时,她从未想过生存竟会是如此艰难。
泛舟黄桥,月色如霜,婉君只觉浑身发冷。
三
婉君从未想到蒋春霖竟是如此之贫穷。
蒋春霖在溱潼的宅子还算不错,可宅子里几乎是空空如也,且积满了灰尘。好不容易请人将宅子打扫干净,杜小舫赠与的盘缠也花了差不多了。好在蒋春霖还有一个朋友,叫陈百生的,不时的来接济一二。蒋春霖却始终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有书就读,有饭就吃,有钱就花。当婉君催急的时候,就让婉君将宅子里的家具卖一些,或者,就是等陈百生送些银两过来。杜小舫太远,否则,蒋春霖大约也会去向杜小舫求告了。
“我只会填词。”蒋春霖这样对婉君说。
厨房里的米已不多了。
婉君淘好米,才想到今天的菜还没有着落。
这几天,他们一直吃的是邻家送来的一瓮咸菜与一小篮子鸡蛋。鸡蛋已经吃完了,只剩下半瓮咸菜。
水云楼。
蒋春霖居然将自己的词集命名为《水云楼词》。
水云楼。
一个多么优雅的名字。
可水与云,又怎么拿来充饥?
更何况,水云楼位于溱潼南郊的古寿寺内,与他蒋春霖何干?就因为他曾经在水云楼里住过一阵?那样的寓居,那样的寄人篱下,使得他念念不忘?“得来湖水烹新茗,买尽吴山作画屏。”这是郑板桥题写水云楼的一副对联。“登临纵目瞰三湖,帆影迷离戏水凫。料得储君居此日,课余闲睡一尘无。”这是孙乔年题写水云楼的一首诗。可是,这水云楼,实在是与他蒋春霖毫不相干啊。虽然说,人生如寄旅,水云楼是蒋春霖人生之中的一个驿站,可一个穷困潦倒的词人居然念念不忘那个如诗如画的水云楼,在婉君想来,也实在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咬得菜根万事足啊。”吃饭的时候,蒋春霖这样笑着对婉君说。
婉君盯着蒋春霖看了一会儿,说:“你很乐观?”
蒋春霖微微地怔了一下。乐观?这些年来的颠沛流离战乱纷乘,又哪里会乐观?“那一年从金陵城逃出来,我曾饿了三天三夜,差一点儿就没命了。”蒋春霖苦笑道,“乐观?我又哪里会乐观?但我们总得活下去。”
婉君说:“那一年,我还是个孩子……”
蒋春霖伸手握住婉君的手:“那样的苦,我们都挺过来了。”
婉君将手抽出,说:“所以,我才不愿再过这样的日子。我不想挨饿我怕饿泥明白吗?”婉君苍白的脸因为激动而略略的显出红晕。
蒋春霖心一痛:“婉君!”
婉君幽幽地长叹一声,脸色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我们总得活下去,可是,爷,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米了。”
蒋春霖迟疑一下:“还有多少钱?”
婉君苦笑道:“陈爷送过来的银两也花得差不多了。”她想说本来我们已没有多少银两可你在数日前竟又买回一批书书钱还欠了一部分没有给得清。可她终究没有说出。
蒋春霖又迟疑一下:“我出去借点儿吧。要不,卖……”
婉君未等他说完,摇头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卖的了,爷。”
蒋春霖默然。
蒋春霖忽就又抓住婉君的手,略带感伤的说:“婉君,跟着我,你真是受苦了。婉君,婉君,你、你不要离开我。我……”
蒋春霖乞求地瞧着婉君。
婉君心头一软,终究还是没有将手抽出来。
眼前的这个老人,终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那些优美的词句,如水一般,时不时地就在他的笔端流淌。
那些词句,换不来米。
可是人活着,总不能只有米。
四
平淡的日子始终都是平淡的,就像没有春风吹过的春水,泛不起一点涟漪。
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蒋春霖时不时地会填一阕新词,让婉君歌唱。然后,这阕新词又会很快地传遍大江南北,传到那些文人墨客是书斋,案头,让那些文人墨客莫名惊叹。起先,婉君也会因此而得意,以为当年的河东君与钱牧斋也不过如此。可接着,婉君就发现,河东君嫁与钱牧斋之后,至少是衣食无忧;而她黄婉君嫁与蒋春霖之后,几乎是日日为衣食而烦恼。
简直就受够了!有时,婉君实在忍不住了,也会冲着蒋春霖发火。每当这时,蒋春霖便会眼巴巴地看着婉君,用一种乞求的眼光。这就又使得婉君的心软了下来。毕竟,眼前的老人是一代才子,词宗,而且,对她确也是一心一意。纵然大多的情况下是冷眼相向,蒋春霖始终都是那样地待她。唉,如果他再年轻三十岁多好,哦,不,即使再年轻二十岁也好。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爱上他的。婉君这样想道。可为什么命运偏偏又要这样的安排?命运将我摆放在你的身边,我会尽我的责任的,即使当初杜小舫替我赎身时候欺骗了我。一代词宗,一代才子。唉,现在,这是一个老人而已。一个穷愁潦倒的老人。
连阳光也是淡淡的,淡淡的暖和,淡淡地照在身上。
婉君倚着墙壁,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做着针线。从前,婉君何尝做过针线来?即使说是做过,也应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还在南京城里,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
一走神,针就在手指上戳了一下,婉君忍不住“哎呦”地叫出声来。
“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正手握一卷《白石道人歌曲》的蒋春霖慌忙放下书来。
“没事。”婉君说。
“流血了。”蒋春霖惊呼道。说着话,忙捉住婉君的手,低头就去吮她的手指。婉君一皱眉头,迟疑一下,低声说:“这样不干净,爷。”轻轻地就将手抽出来,在衣襟上擦了擦。蒋春霖有些不知所措,说:“那,我帮你包扎一下。”婉君白了他一眼,说:“不用了,已经好了。”站起身来,倒了点水,将手指冲洗干净,然后用毛巾轻轻的拭干。回头再看蒋春霖,正呆呆的,发愣。
“婉君,”蒋春霖忽就神情黯然,落泪道,“婉君,我是不是很没用?我、我……”
婉君叹息道:“爷,你说什么呢。”
蒋春霖长叹一声,道:“我明天去一趟苏州。”
婉君问:“去找杜……”
蒋春霖点头,说:“他的词集,是我帮他删订的。或许,能够要些润笔。”说到润笔,蒋春霖不觉老脸微红。
婉君也叹了口气,声音略略的柔和了一些,道:“爷,也只能这样了。不然,我们、我们真的很难生活下去啊。”
五
蒋春霖搭船到苏州去了。
蒋春霖走后,婉君依旧是每日接些针线回来做,虽说做得慢,毕竟还能做些,且渐渐地就做得熟练了。只是,做针线的收入终究有限,每日三五文、七八文的,最多一日也不过十文钱。每到这时,婉君便会想起她的歌女生涯。每到这时,又会猛然警醒:神女生涯魂是梦,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这一日,婉君将做好的针线送到衣铺,回来时顺便去买些新鲜的蔬菜。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是以咸菜度日,婉君觉胃里直翻酸水,一闻到咸菜的味道就想呕吐。蒋春霖到苏州已四天了,还未回来。
“黄婉君!”婉君正与菜贩子讨价还价的当儿,忽听得背后有人喊她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就回头。
蓦回头时,婉君如遭电殛一般,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
喊她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那男子似笑非笑,脸上洋溢着一丝兴奋。
婉君当然认得这个男子。
当蒋春霖带着婉君住到溱潼之后不多久,婉君便开始与这个男子打交道了。
这个男子是泰州一个盐商的账房。当蒋春霖还在任上的时候,与这个盐商颇为交好;所以,当蒋春霖卸任的时候,这个盐商表示,他愿意每个月都资助蒋大人一些银两。问题是,以蒋春霖的性格,自尊,又哪里愿意去打这样的秋风?可要是拒绝这笔银两,生活又怎么办?对于穷人来说,自尊实在是奢侈品,看着好看,实质上却起不到丝毫作用的。
于是,那每一个月去盐商账房领取一些银两的事,就落到了婉君的头上。
去了几次之后,婉君便再也不肯去了。蒋春霖有些好奇,却也不敢问一个原因,再叫上陈百生托人送来一点银两,暂时还算能生活下去,蒋春霖便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或许,是因为路太远,婉君怕累吧。蒋春霖这样想道。从溱潼到泰州,终究也有小半天的路。而婉君一个弱女子,又何尝独自走过这么远的路?
蒋春霖没有问,婉君自然也不会再去想。
她以为,她已经将那个人忘记了,就像忘记歌女生涯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恩客一样。
现在,她已从良,早不是从前那个任人凌辱的歌女啊。
“你真的是黄婉君?”那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婉君。
“你……”婉君又羞又急,下意识地往四周看,生怕被什么人看到似的。青石街上,人来人往,黏黏地叫卖声、招呼声,缕缕不绝。
没人在意到婉君,以及拦在婉君身前,涎着脸说话的那个男人。
“我怎么了?”这个男子开心地说道,“婉君小姐不认得我了么?”
“我……”
“婉君小姐不记得我没关系,可是我却没敢忘记婉君小姐啊。呵呵,是魂牵梦萦啊。只不知后来婉君小姐怎么就没来泰州呢?老爷可没说不给这笔银两啊。”那男子道,“后来,我也托人想找婉君小姐来着,却怎么也没找到,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遇,也是有缘。婉君小姐,我是不是有请你喝茶的荣幸?”
婉君有些怔怔。
当初,她就是为了躲避眼前的这个男人,才再也不去泰州那盐商府上的。婉君清楚地记得,当她第一次出现在那盐商的账房里的时候,眼前的这个男人,也就是那位盐商账房里的账房先生,眼睛一下子就直了。这个男人,百般殷勤,眼睛片刻也不肯离婉君那张略显沧桑的脸。婉君做过歌女,又哪里还不会明白这个男人的心思?当这个男人越发殷勤的时候,婉君害怕了,于是,便选择了再也不去泰州。
想不到,居然在溱潼重遇。
婉君脸色苍白,有些心虚。
其实,我们之间真没事。婉君转念又这样想道。
“婉君小姐,给个面子吧。”那男子殷勤地说道。
跟当年一样,那目光还是那样的灼热,人,还是那样的殷勤。可没由来的,婉君的心境竟忽然之间有了极大的变化。她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可恶,更不是那么猥琐。她不知道到底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变了,还是她自己变了,她只知道,等她的心略略平静之后,她发现,她从前对这个男人的厌恶,现在,居然已经没了。
那男人笑道:“呵呵,婉君小姐,我没有其它意思,只是请小姐喝碗茶,真的。”
婉君的心里忽就有些古怪的感觉,再看眼前的男人,居然怎么看都比蒋春霖顺眼,便迟疑道:“这可能不大好吧。”
那男人一笑:“请,婉君小姐。”
溱潼只是一个小镇,位于溱湖边上。清凌凌的溱湖水,水面上水鸟扑腾,使得水面泛起一圈圈的涟漪。
婉君的心,她以为久已尘封的那颗心,在那男子将她引进茶馆的时候,居然也泛起这样一圈圈的涟漪来。
那男子一进茶馆,便吩咐泡上最好的雨前龙井。四溢的茶香,即使是不会饮茶的,也会心旷神怡。婉君虽说没有饮茶的癖好,可这样的茶香还是使她忍不住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好香。”
朦胧的茶烟中,那男子却是紧紧地盯着婉君的脸。那火辣辣的眼光使婉君的脸又是一红,同时,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与满足。
那男子忽地叹了口气,说:“这两年,我找遍了泰州,还到南京、扬州,一直都在找寻婉君小姐……”
婉君脸色微变:“你……”
“让我把话说完,”那男子目光炯炯地说道,“你知道这种相思的滋味吗?从见到你开始,我就知道,我要死了。”
这是《西厢记》里张生初见崔莺莺时说的话。那那男子现在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婉君便是再想装糊涂也不可能了。
“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婉君不敢听他把话说完,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出了茶馆。
“婉君小姐……”那男子在身后大声叫道。
婉君稍稍停顿了一下,究竟没有回头。
六
一连几日,婉君俱是心神不定。也许不为什么,也许是为了什么,可婉君说不清。或许,是那男子比蒋春霖年轻几岁?还是因为那男子这几年一直都在找她?一个女人,始终都有一个男子在牵挂着,终究是一件叫人愉悦的事情。
即使一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她只知道,他是那位泰州盐商的账房先生,是一见到她就“要死了”的男人。
她相信他的这种感觉。
因为在这个时候,她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或许,在蒋春霖的心里,她也会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吧。可她始终没有忘记,她只是杜小舫送给蒋春霖的一件礼物而已,是一个词人送个另一个词人的礼物而已。
没人去问她愿不愿意。
无论是现在高官得做的杜小舫,还是现在一无所有的蒋春霖。
没人在意她的感觉。
她知道,蒋春霖或许是真的很喜欢她,但她更知道,蒋春霖决不会在意她是不是也喜欢他。
就像一个人喜欢一朵花,却决不会去想这朵花是不是喜欢那个人一样。
这使得婉君很是悲哀。
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蒋春霖还没有回来。
婉君打扫书房的时候,无聊地将蒋春霖的手稿整理了一下,然后,读到一阕《谒金门》:
人未起。桐影暗移窗纸。隔夜酒香添睡美。鹊声春梦里。妆罢小屏独倚。风定柳花到地。欲拾断红怜素指。卷帘呼燕子。
重读几遍,婉君痴痴的,发了一会儿呆。她明白,蒋春霖漂泊一生,现在,是将所有的感情寄托在她身上了。甚至于她也相信,即使是那位表示找了她两年的男子,也不会有蒋春霖这样深情:艰难的生活里,有时只剩下一个鸡蛋,蒋春霖也会留给她。蒋春霖的笔下,心里,不知留下多少婉君的名字。
算了,不要胡思乱想了,那人终究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是过客,终究会离去。
然而,过客竟没有离去。
不但没有离去,反而找上门来。
这就使得婉君大吃一惊,同时又有些惊惶。
“我不会放弃的,婉君小姐。”那男子这样说道,“我打听了这几日,总算又找到了婉君小姐,呵呵,这也算是有缘吧。--原来,婉君小姐嫁的是鹿潭先生。”
婉君说:“你认识外子?”
那男子笑道:“大江南北,谁不知道大词人蒋鹿潭啊。套句古话来说,凡有井水处,无不歌蒋先生之词也。只是,蒋先生好像年纪已经很大了吧?”
婉君说:“你想说什么?”
“哦,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没想到蒋先生竟清贫如斯,穷苦如斯,呵呵,一代大词人,穷愁潦倒,真是叫人百感交集啊。我来看看,如果婉君小姐,哦,不,是蒋先生,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会尽力的。”张南说着话,依然是用一种灼灼的目光紧盯着婉君。
婉君淡淡地道:“多谢先生关心,不过,我们很好,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那男子微笑,微笑中透出一丝诡异。
婉君抑制住心头一丝怪异的念头,对那男子道:“外子不在家,先生还是请回吧。有什么事,等外子回来再说。”
那男子依然微笑着:“我不会放弃的,婉君小姐。”
七
蒋春霖终于回来了。
可蒋春霖居然是两手空空地回来。
婉君一颗心就沉了下去:“怎么回事?”
蒋春霖嗫嚅道:“小舫的手头也不宽裕……”
婉君的脸也就沉了下去,不再看蒋春霖。
“婉君……”蒋春霖陪着笑。
婉君站起身来,冷冷地说道:“我煮饭去。”
一连几日,婉君都没有理睬蒋春霖。蒋春霖却也是好耐心,说着绵绵情话:绵绵情话从蒋春霖嘴里出来,婉君虽说有些好笑,也未免另有些感动。
算了。婉君心里这样想道。毕竟,我也三十出头的人了。就这样吧。虽说清苦,可蒋春霖这几年确实是对她极好。认命吧。
蒋春霖说:“我将《水云楼词》编一下,送到书肆,或许,能换几个钱。”
婉君就好笑:“现在还有多少人读词啊?”
蒋春霖正色道:“这一点我有自信。我的词,本朝一流。本朝词人,我也只服湖海楼、金风亭长、纳兰容若数人而已。”说到词,这位老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来。
婉君说:“我信。可是,你的词再好,也没法子吃啊。--别说我俗,爷,俗人要吃饭,雅人也要吃饭的。”
蒋春霖说:“从前你不是这样。从前,你唱的词多好啊。”
婉君叹息,幽幽道:“从前,不需要为衣食烦心的。”
蒋春霖默然,良久,道:“婉君,我刚刚做了一阕词,你唱来听听……”便乞求地看着婉君。
婉君也默然。
“婉君。”蒋春霖求告着,将一纸词笺递给婉君。
词笺上,是一阕《八声甘州》:
又东风唤醒一分春,吹愁上眉山。趁晴稍剩雪,斜阳小立,人影珊珊。逼地依然沧海,险梦逐潮还。一样貂裘冷,不似长安。多少悲笳声里,认匆匆过客,草草辛盘。引吴勾不语,酒罢玉犀寒。总休问、杜鹃桥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云暗、任征鸿去,莫倚栏杆。
蒋春霖说:“我来操琴。”
琴声悠悠响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按着琴音,婉君忍不住低低的哼唱。一曲唱罢,婉君只觉胸口难受,想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好!”忽就有个声音在门外响起。
然后,一个男子,一个人到中年却比蒋春霖要显得年轻得多的男子,施施然地推门进来,满脸含笑。
“我姓张,张南,”那男子微笑着,“这位老先生想必就是大词人鹿潭先生了。真真是好词。鹿潭先生的词好,婉君小姐唱得更好。呵呵,真真是双绝啊。”
八
“这人是谁?”
“……他说他叫张南。”
“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哼哼,婉君小姐,叫得好亲热。”
“……是马老爷府上的人,”婉君低声解释道,“前几日,在市场上遇到。”
“就这些?”
“就这些。”
“嘿嘿,那他怎么找到我们家来了?嘿嘿,带来这么多的东西,还有金钗。还有……”
婉君抬头,颤声道:“爷,你想到哪儿去了?”
“……真的?”
婉君憋气道:“假的。”
蒋春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忽地落泪,说:“婉君,我、我不是疑心你怎样,可我、我、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失去你。婉君,婉君,你可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婉君,你不能离开我。我、我不能没有你。”
婉君默然良久,道:“爷,这些话,你也不用说了。婉君不会离开爷的。虽说我是歌女出身,可我也知道嫁鸡随鸡的道理。”
“婉君……”蒋春霖颤着手,轻轻地将婉君搂在怀里。
“婉君,你是我的,婉君,我绝不能没有你。”蒋春霖喃喃自语道。
一场小风波过去,吃罢晚饭,又说一会闲话,婉君觉得疲倦,很快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蒋春霖却怎么也睡不着。
今夜是残月。虽说是残月,依然是朗朗的照着,直照得满地霜雪。冷冷的霜雪,一如蒋春霖此刻的心。
不会的。蒋春霖对自己说道。
月光照在婉君熟睡的脸上,婉君的眼角已有一丝丝的皱纹了。
这些年来,婉君确实是受苦了。可是,她总不会因此而不安于室吧?不会的。肯定不会的。蒋春霖继续这样胡思乱想着。这样的胡思乱想,使得蒋春霖的心隐隐发疼。
那张南究竟是怎么回事?
婉君终究是歌女出身。
蒋春霖呆呆地倚靠在床头,浑不觉夜已深,天渐寒。
九
“你究竟想干什么?!”婉君气急地问道。
婉君跟往常一样,将做好的针线给衣铺送去;蒋春霖却跟往常不一样,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她。说是紧跟着她,手里竟还握着一卷《饮水词》。婉君几次让他回去,终究不肯,只是猥猥琐琐地跟着,也不做声。那猥琐的样子,直叫婉君皱眉,终于忍不住发作。
蒋春霖陪着笑,吞吞吐吐地说:“我陪你去。”
婉君说:“我用不着你陪。”
可蒋春霖还是陪在她的身边。
一路上,有与婉君相识的,便问,太太,这位老先生是谁呀?
因为蒋春霖的打扮实在不像是老仆。往日里,蒋春霖很少出门,只是在家读书、填词;偶尔出门,也是诗朋词友的雅集,或者索性到苏州或南京去,与街坊无缘相识,自然,街坊也不认得这位江南第一大词人。街坊认得的,是婉君。
婉君就尴尬地笑,低声说:“是我们爷。”声音直低得叫人听不见。
蒋春霖呢?听见街坊说“老先生”三字,也觉尴尬,觉不是味儿。
“求求你,你先回去吧。”婉君低声哀求道。
蒋春霖犹豫片刻,轻轻地却又是坚决的摇头。
“你到底想干什么?”婉君几乎是愤怒地问道。蓦然心头一动:“莫非、莫非你……”她压低了声音:“你不放心我?”
蒋春霖有些慌乱。
婉君冷笑一声:“你担心我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蒋春霖还是不做声,可他的眼里分明写着的就是这层意思。
这回婉君是真的愤怒了,嘴唇动了几动,却眼圈一红,落下泪来。
见婉君落泪,蒋春霖也不由心慌:“婉君……”
婉君恨恨地冷笑:“原来在你的心里,我竟是这样淫荡的女人!嘿嘿,我算是明白了!”说罢,头也不回的,回家去了。
蒋春霖急急地跟上,但年纪大了,又哪里跟得上去?疾走不过十数步,已是气喘吁吁,显出气急败坏的样子来。等赶回家,早已是喘不过气来,胸口起伏不定。
“婉、婉君,我、我不是这个意思。”蒋春霖解释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见蒋春霖如此之狼狈,婉君又有些心疼。毕竟,在一起已好几年了。
蒋春霖又大大地喘了口气,使胸口渐渐地平复一下,说:“我、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
婉君冷笑:“你把我当小孩子啊?”
蒋春霖愣了愣,说不出话来。
蒋春霖本来就拙于言辞,现在,就更加不知如何说了。
半晌,忍不住也落泪,说:“婉君,我、我实在是不能失去你……我宁愿不要我的命,也不能没有你。”
婉君呆呆地,再次落泪,低声说:“我知道,爷。”
“婉君。”蒋春霖捉住她的手。
婉君幽幽的叹息,没有将手抽出来。
一双虽说略显苍老却依旧白皙的手,在一双满是青筋的粗糙的大手之中。蒋春霖轻轻地抚摸着婉君的手背,叹道:“对不起,婉君,我、我真的老了,多疑了,害怕,害怕你会离开我。对不起,婉君,对不起,我不会再这个样子的。不会。”
十
蒋春霖是不再跟着婉君出门。
然而,婉君的每一次出门都使他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仿佛是一次小小的死亡。不过十来日的工夫,蒋春霖比先前要憔悴得多、苍老得多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蒋春霖喃喃自语,每日每夜。有时,是在婉君出门的时候,有时,就附在婉君的耳边。这使得婉君奇怪。婉君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像年轻小伙子一样的絮絮叨叨着绵绵情话,有的情话甚至可以说是肉麻,尤其是从蒋春霖略显干瘪的嘴里说出来。
然而,情话说得多了,听得多了,婉君终究有些感动。
对于女人来说,总是喜欢听情话、听好听的话的,无论这话是出自一个老人还是一个少年。
尤其是对于年过三十的婉君来说。
蒋春霖已经老了,可婉君岂非也正在渐渐的老去?
差不多一个月没见张南来纠缠了。那张南来纠缠的时候,婉君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现在,不见张南,婉君居然又有些失落。
也许,张南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一个点缀,同以往所遇到的过客、点缀一样,悄悄地出现,又悄悄地消失。
蒋春霖的多疑多虑,固然使婉君生厌,然而,又何尝不使她有些许的甜蜜?
大约人世间的事情都是如此,有其一面,就必然有其另一面。
婉君已经习惯了蒋春霖的目送她离家,再目迎她回家。
一个老头,手握一卷线装书,倚门眺望,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街坊们也渐渐地认识了蒋春霖。
很少有人知道蒋春霖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词人,——即使知道,也不会以为一个老词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溱潼人喜欢的是渔歌,是拔根芦柴花,可决不是那什么《水云楼词》。
街坊们先是惊奇:婉君你相公是这么一个老头?才子?即使是才子,也是老才子了。
然后,街坊们又赞叹不已:婉君,蒋先生虽说老些,可对你真的不错。哪像我们当家的,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你看,你看,这就是昨天打的,简直就是往死里打。
是呀,是呀,我们家那混蛋,刚刚有了两个钱,就想娶小!
婉君苦笑着说:我就是小。我是妾。
啧,啧,可人家蒋先生只有你一个女人是不是?只有你一个,这大小又有什么分别?女人啊,有男人这么疼,应该知足了,这一辈子也不枉过了。
………………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
也许,生活还会这样,平淡而清苦的过下去。
——如果张南不再出现的话。
十一
张南的再次出现依旧是悄悄然地,悄悄然地,就出现在婉君的眼前。
“婉君小姐,”张南笑容可掬地说道,“有一笔生意,出去了一趟,还算是赚了一笔小钱。--婉君小姐,能不能请你喝茶?”
婉君叹道:“张先生请你不要再纠缠了好么?算我求你了。”
“纠缠?”张南睁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婉君,说,“我没有纠缠,也不会纠缠婉君小姐的,我只是想请婉君小姐喝杯茶而已。”
婉君怒道:“我不会去的。请你让路!”
张南依旧盯着婉君,缓缓道:“我只是想看看婉君小姐,想每天都能看到婉君小姐而已,别无他意。还有一件事,是要告诉婉君小姐的,我已经将家搬溱潼来了。”
婉君一惊。
张南淡淡地道:“就在贵府所在的那条街上。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婉君小姐了。呵呵,知道么?从第一次看见婉君小姐美丽的容颜,我就想,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婉君小姐的了。唉,我终究是无缘,无缘与婉君小姐厮守,可是,天可怜见的,却让我在溱潼遇见婉君小姐。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想与婉君小姐同住溱潼,能时常见到婉君小姐而已。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有。婉君小姐,这怎么能够说是纠缠呢?再说,我多少也还有些积蓄,也许必要的时候,还能够帮婉君小姐一把。”
婉君呆呆地听张南把话说完,一时无语。
她发现,此刻,她根本无法说什么。
叫张南离开溱潼?
“其实,我已经老了。”婉君说。
张南眼里放出光来:“我却觉得你年轻。”
婉君苦笑:“我真的老了,张先生,不值得你这样。”
张南说:“蒋先生却更老。”
婉君微微变色。
张南续道:“我可以等,等蒋先生故去,等一个属于我的机会。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婉君脸色又是一变,良久,强笑道:“那时,我真的是一个老太婆了。”
张南笑:“也许会。也许不会。”
婉君心念一闪:“你想干什么?”
张南先是一愣,似是不明白婉君的话,然后恍然,迟疑道:“我看,蒋先生的身体似乎不是很好……”
婉君摇头,说:“我不会背弃我相公的。张先生,你的心意,我谢谢了,只是,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从前,我只是一个歌女,现在,是蒋先生的小妾。……我只是残花败柳,不值得的。”
说罢,也不等张南回答,转身疾走。
“婉君小姐!”张南在身后疾呼。
婉君稍稍犹豫一下,头也不回。
十二
下午,蒋春霖将自己的词稿整理了一小部分,想,检点平生所作,究竟会有多少传世?但不管怎样,在词史上,必会有浓重的一笔的。对于词,蒋春霖终究还是有相当的自信。婉君终究会因为《水云楼词》而不朽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聊补这些年来的愧疚:婉君确实是受苦了。这样清贫甚至可说是凄苦的日子,如果没有婉君陪伴在身边,也许,我自己也忍受不了了。蒋春霖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头又渐渐的疼了起来。
“婉君!”蒋春霖叫道。恍乎间,他已不记得婉君出门了没有。
“婉君!”蒋春霖一边呼唤着一边出了书房。
“婉君!”呼唤婉君的名字,蒋春霖心头就充满了温馨。
先前的那些个疑心,这些天已烟消云散。
“因为我太在乎你,所以,我疑心,所以,我恐惧,害怕,害怕你离开我。”蒋春霖不断地向婉君重复着同样的话。也许,只有这样的重复,才能将心头的意思深深地表达出来。
婉君不在。
蒋春霖一手摁着鼻梁,一手抓着那卷还未修订好的《水云楼词》,缓缓地踱进正厅。正厅也显得空空落落的。蒋春霖左右打量了一下,将《水云楼词》放了下来,然后抓过一块虽说残破倒还干净的毛巾,到院子里又打了一桶冰凉的井水,将毛巾浸湿了,然后使劲地擦拭酸疼的鼻梁骨。
一阵冰凉的感觉,酸疼似乎要好了些。可将毛巾拿下的时候,却还是一样的酸疼,甚至比刚才要更厉害些了。
又狠狠地擦拭了几把,酸疼不见减轻,蒋春霖就有些失望,又有些难受。
“婉君……”蒋春霖低低地哀叹。
婉君还没有回来。
这时,天色却似乎渐渐地阴暗了下来,而且,有阴冷的风。
蒋春霖就越发地头疼了。
搬过那张早已不知修补了多少遍的藤椅,蒋春霖在院子里坐下,将院门打开,忍着头疼,不时地望着婉君归来的路。
每一次,当看见婉君在院门外的青石路上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与欣慰啊。
头,却还是隐隐的疼着。虽说不是很疼,却一直都是,一直都没有停止。
这样无休无止的酸疼就使蒋春霖感到一阵不安。
这么久还不回来,莫非……
蒋春霖几乎就是一身冷汗。
正在这时,远远地看见婉君急匆匆地回来。
十三
疑心像一只小老鼠一样,直在心里挠个不停。
婉君气恼地回来,什么也没说。中午,只是胡乱地用开水泡了饭,就着昨晚吃剩下的一碟乳腐,算是吃了一顿。
婉君说:“爷,你要是再不想想法子,我们真的只有吃西北风了。”
这些年,家里值钱些的家具,婉君的一些首饰,都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如果再不弄到银两的话,下面,真的只有吃西北风了。
蒋春霖说:“嗯,我会想法子的。”
婉君冷笑道:“想法子,你想什么法子啊?爷,我做些针线,实在不够我们吃饭的。再说,一个男人,靠女人养活……”婉君说到此,意识到什么,忙住了嘴。蒋春霖已自脸色剧变。
“婉君!”蒋春霖颤声说道,“你、你竟这样看我!”
不由自主地举起手来,一巴掌就要落下。
巴掌却终究没有落下。
婉君叹道:“爷,不是我……唉。”
婉君深深地叹息。当初,杜小舫说,蒋春霖曾经做过盐官,大清朝的盐官哪个不是家财万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却不料,蒋春霖这个前任两淮盐大使竟穷苦如斯,差不多就只有这一座空空落落的院子了。
“算了,”婉君苦涩地说道,“我去睡一会儿了。”
说完也不再理蒋春霖,自顾自的进了卧房,顺手将门狠狠地关上。“砰”的一声巨响,使蒋春霖不由自主地心头一跳。呆呆的发了一会儿愣,蒋春霖几乎就要落泪,强忍住了。
为什么会这样?先前,婉君一向都是很柔顺的。这些天,怎么变得越来越喜欢发脾气?午前出去送针线,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
蒋春霖越发地头疼,疼得忍不住轻轻地呻吟一声。
“婉君!”蒋春霖走到卧室门口,轻轻地呼唤。
卧室里没有动静。推门,又推不开。婉君将门从里面反锁了。
“婉君!”蒋春霖低声说道,“我、我头疼……”
依然没有动静。
蒋春霖呆呆地在门外站了一阵,心头一阵阵气苦,赌气道:“婉君,你真的是嫌我老了?是,我又老又穷,是值得你嫌弃的了。你是不是还巴不得我早点死掉,你好赶着去嫁人?……”
婉君依旧是不做声。
蒋春霖不觉就心灰如死。
摁着更加酸疼的鼻梁骨,蒋春霖茫然地出了门。
门外,青石路泛着寒光,一如蒋春霖此刻的心情。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蒋春霖头疼欲裂,心头凄苦,漫无目的地在青石路上胡乱地走着,自己也不知自己想到哪儿去。
天就渐渐地暗了下来,仿佛要下雪。往年,每当下雪,都会惹起几许词心,催生几阕新词。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古来不知多少名词佳构,都与雪有关。雪的洁白,雪的晶莹,雪的清冷,都使人词心顿现。可是现在,蒋春霖只觉清冷,哦,不,是一种刺骨的冷,冷得他的心直发颤。
为什么会这样?
莫非婉君真的因为贫苦而不安于室?
蒋春霖不但头疼,连心也隐隐地发疼。
“啊,是蒋先生吗?”恍惚中,蒋春霖听得一个热情的声音,“是蒋鹿潭蒋先生吗?”
蒋春霖迷迷糊糊地转头,猛的就一惊,然后浑身发冷。
“是你?!”蒋春霖几乎就要叫出声来。
“是我啊,鹿潭先生,”说话的自然便是张南,“我搬到溱潼来了,就住在那边,今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呵呵,鹿潭先生,我还想拜先生为师,跟先生学词呢,先生可不要嫌弃我哦。鹿潭先生的词,我一向喜欢的……”
蒋春霖脑子里嗡嗡地乱鸣,已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了。
十四
蒋春霖恨恨地踢开院门,疾步到卧室门口,又是一阵猛踢。
起先,婉君没有动静,最终还是忍不住将门拉开:“爷,你疯了?”
蒋春霖瞪着血红的双眼,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冲着婉君吼道:“我总算明白了!总算明白了!”
婉君说:“你明白什么?”
蒋春霖浑身都在发颤,用手指点着婉君,道:“原来、原来你跟那小子、跟那小子……”蒋春霖喘着气,变得面目狰狞。
婉君皱眉:“什么那小子?”话未说完,心念一动,不由也瞪大了眼。
蒋春霖冷笑:“装什么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原来你跟那小子已经串通好了!嘿嘿,是不是正想等着我早些死啊?好让你们快意?!都搬到家门口来了,好天天相会了是不是?是不是还想学潘金莲啊……”一串恶毒的话从蒋春霖嘴里喷了出来,几乎就不让婉君有说话的机会。
“潘金莲?!”婉君的心一阵揪痛,“你说我是潘金莲?”
蒋春霖说:“比潘金莲也好不到哪儿去!西门庆都到家门口来了,都到我们家来了,我居然还相信你,我、我真是瞎了眼了……”蒋春霖忍不住就泪如雨下。
婉君气怒交集,已自说不出话来。
蒋春霖又抡起巴掌,在空中顿了顿,却狠狠的打在了自己的脸上:“我、我真是瞎了眼了!”说罢,整个人无力地臃倒在婉君的脚下,眼泪在苍老的脸上流淌。刹那间,婉君觉得蒋春霖是越发地苍老了。
蒋春霖的哭声终于渐渐地小了下来。
婉君的怒气也渐渐地小了,而转为可怜。
“爷,”婉君蹲下身来,说,“爷,你多心了,这根本是没影的事儿。”
蒋春霖眼泪汪汪:“你、你跟那个张南、那个张南……”
婉君叹道:“我根本就没理他,爷。”
蒋春霖捉住婉君的手:“你真的不是潘金莲?”
婉君生气的说:“爷,原来你真的这样看我!我像潘金莲吗?”
“我不知道。”蒋春霖可怜巴巴地说,“可是婉君,不管怎样,我都不让你离开我。”
婉君轻轻拭尽蒋春霖脸上的泪水,说:“我不会的,爷。你实在是多心多疑了。相信我。”
蒋春霖却实在难以相信。
一方面,他实在难以相信婉君与张南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婉君。休妻?这是他想都不敢想,一想就心疼的。
那么,怎么办?
紧紧地将婉君搂在怀里,苍白的灯影映在他苍白的脸上。
天色昏暗,而阴寒;看样子,真的是要下雪了。
雪还没有落下。
婉君稍稍地挣了一下,没有能够挣脱,便不再动。
“婉君,”蒋春霖低声呼唤着,“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对不起,婉君,我太冲动了,婉君……”
婉君苦笑:“我已经习惯了,爷。”
蒋春霖凄然道:“是我的错,婉君,是我没有能够使你过上好一些的日子,……跟着我,几乎就是吃糠咽菜,……可是婉君,我对你是真心的,我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失去你。答应我……”
“答应什么?”
“不要离开我,婉君,不要!”
婉君心不在焉地道:“不会的,爷,天色不早了,早些睡吧。”
“嗯,”蒋春霖迟疑地说道,“过几天,我再到苏州去。”
“嗯?”
“从杜小舫那儿……”
婉君打断了他:“过几天再说吧,爷。现在,还是睡吧。啊,看样子要下雪了。”婉君从蒋春霖的手臂中挣脱了出来。
“我不习惯这样睡的,爷,这你知道。”婉君歉然道。
并头躺在床上,两人各自心思,不再说话。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十五
雪真的就纷纷扬扬的下将起来了。一夜之间,整个儿的天地是洁白的一片。然而,这样的晶莹与洁白使蒋春霖一阵阵地觉得凄冷。
望着婉君几乎可以说是漠然的脸,蒋春霖忽就又要落泪。
“婉君,”蒋春霖深深地叹息道,“我真的对不住你,跟我一起受这么多的苦。”
婉君说:“只要你不瞎疑心就可以了。”
蒋春霖说:“我不会了,婉君。--我今天就到苏州去吧。”
婉君一怔:“在下雪!”
“雪还不大,没事。而且,一船风雪,也是诗情画意啊,呵呵。”蒋春霖强作笑意,说道,“这一回,我一定,嗯,一定--”蒋春霖一想到向杜小舫索要银两,终究有些赧然。虽说他们是极好的朋友,而且杜小舫的词集由他审定,索要润笔也未尝不可。上一次去,杜小舫热情招待:苏州古城,几乎游玩个遍。蒋春霖最终没有提自己的困难,除了一些苏州的土特产,几乎是空手而归。他明白,上一次他使婉君失望。
婉君鬟髻上的金簪也早已变卖掉了,现在,婉君的鬟髻上只斜插着一朵绢花。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蒋春霖忽就想起这两句诗来。
“婉君,”蒋春霖深情地说,“真的委屈你了。--即使、即使……我也不会怪你的。”
蒋春霖吞吞吐吐的,心头的疑心又哪里会散去!
婉君叹道:“爷,你终究还是、还是不放心我。”
蒋春霖尴尬地说:“不……”
婉君冷漠地道:“你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收拾一下,我跟你一起去苏州吧。”
蒋春霖越发地尴尬了。
带着忐忑不安,蒋春霖上了去苏州的客船。
蒋春霖终究没有带婉君一起走。
他明白,如果带着婉君一起上船,便是分明把自己的疑心告诉给了婉君:这肯定是婉君所难以接受的。然而,把婉君溜在溱潼,蒋春霖的心又是隐隐地疼。
但愿只是疑心。他对自己这样说。但愿我是错的。
我会很快回来的。他又这样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不会空手回来。我还要托杜小舫刻印《水云楼词》,《水云楼词》终究会卖出一些的。我不能使婉君失望。
闪念之间,蒋春霖不由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何以是“千金散尽”。太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可事实是,千金散尽不复来的。
雪轻轻地打在船蓬上,雪落无声。
芸香社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