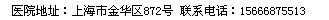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胃反酸 > 疾病常识 > 青春五部曲往事如烟之小学时光
青春五部曲往事如烟之小学时光
往事,好像很久之前看过的一场电影,听过的一首歌,虽然很难完整地记忆、复述,整个线条在平日里甚至非常模糊,可是一有机会,有一些片段,却会在猛然之间突然变得异常清晰。这些片段,有的稀松平常,有的颇为精彩,日久弥新。在静静的夜里,在旅途中的车里,它们会突然跳进脑海,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一)
毛泽东主席去世的那年,我不满12岁,在小学五年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消息的那一天上午,我们班的学生由老师带领去大园子生产队劳动,全班同学从高梁地里把成捆的高粱秸杆往打麦场里扛。
这是我当年很害怕的活儿,一捆潮湿并带有发霉味道的高梁秸杆扛在肩上,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而言,不但份量沉重,而且尘土枝叶渣子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浑身便不停的发痒,让人难受不已。
干完活后我们这些小学生们被分配到社员家里吃饭,每家的饭都不相同。吃完饭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时分,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往回走。
出了劳动的村庄,队形立即散了,三五成群唧唧喳喳乱喊乱叫你追我赶乱打斗。过了小河子沟到新店子地界时,听到公社大院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着什么。不知哪位同学喊了一句“毛主席死了”,马上有同学大声制止:“这是反动话,不能说死,是逝世。”
立即,吵闹声静了下来,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开始叹息,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生还哭了起来,说毛主席逝世了,她家又要挨饿,她妈的病好不了啦……年龄小的同学则低着头,哧哧的偷笑,并拿手里的树枝相互戳捣。有一些同学则小声说不许笑,笑也是反动。
那个时候,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相差很大,在一个班里,大的有十四、五岁,小的则只有十岁左右。
快到学校门口时,大家四散而去,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到前河畔的土堡子里垒碉堡去了。直到天黑下来才回到家。
(二)
家里已点起了灯,厨房里笼罩着水蒸气和烟雾,这是我最喜欢的场景。饭已经熟了,母亲在厨房门口站着,父亲在上房用柳枝条编筐,我奔到上房大声告诉父亲毛主席逝世了,父亲抬起头瞪了我一眼,没好气的说你胡嚷啥?赶紧吃饭。
我家是大家庭,有十口人,吃饭时父亲和大哥还有四岁的五弟在炕上,炕桌上会摆放一小碟咸菜,有时还有辣子油、蒜、葱等奢侈品。二哥蹲在炕头或者门槛上,我和四弟则把饭碗架到屋里的方桌上,偶尔怯生生的到炕桌上夹一点咸菜。母亲和四姐经常在厨房,母亲有时会在饭快吃完时才坐到炕桌边。吃饭中间听大哥给父亲说主席去世的事。饭后父亲严厉地宣布,到外面都不要胡说这事。
(三)
过了好多天,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黑布套套,说是叫黑纱,给毛主席开追悼会时要戴在左臂上。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黑纱,大家领到后觉得很好奇,都焦急的盼望着开追悼会。
追悼会是在一个教室里开的。参加的人数总共六、七十人,四、五两个年级的学生大约五、六十人,老师十人左右。我现在只记得孙思明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稿子,略带着哭腔,缓慢的念着,那是在致悼词。
有几个老师在哭,学生中几个年龄大些的也有哭的,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低着头乜斜着眼睛偷看,在我旁边站着的贾牛儿突然咳嗽了一声,扑腾一声流出了长长的两绺鼻涕,我掐着自已的肚皮极力忍住笑,牛岁旦偷偷的把唾液吐在手指,抹到眼睛上装哭,并用两只脏手把眼圈揉的红里透黑……孙思明老师念完稿子后,王校长也讲了什么,整个气氛很安静,大家都静静地站着,没有平时开会时的交头接耳。
宣布追悼会结束后,大家按队形慢慢走出了教室。
(四)
追悼会过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的一个早晨,好像是星期日,太阳已升得很高了,我从家里出来蹓跶到学校。
学校就在我家院子旁边,两三分钟的路程。
孙思明老师在大教室门口喊我,我走过去一看,是学校办墙报专栏,贾牛儿也在,他用毛笔抄写大字报,还有几个学生和老师,有的在写有的在画,大家都很兴奋,场面很热闹,现在记不清是谁了!
孙老师给我分派了任务,让我用毛笔抄写两份大字报。他正在画一幅漫画,是一把大铁锤和一个大拳头,下面砸了三男一女四个人,标注是王张江姚。
我很兴奋,立即投入抄写工作。
那时候,我和贾牛儿年龄小,但是因为毛笔字和粉笔字写得都还行,办黑板报和墙报专栏的事一直是我俩帮老师干。抄写大字报的时候,孙老师说,王张江姚四个人是四人帮,是反革命,害了毛主席,现在要批判。
快中午时,我们把大字报和漫画拿到学校的围墙外面,按照老师的规划,用浆糊贴到墙上,立即围上来好多人观看。
此后学生们一直议论四人帮。有一个年龄大的同学告诉我们,王洪文有手枪,江青的头上是假发,是野狐精变的,很厉害,没有人能治住,是许世友藏在人民大会堂的房梁上面抓住的。还有同学说,毛主席是江青害死的,主席病了,江青不让睡觉,一直拉着主席翻过来翻过去,结果把主席翻死了。
(五)
那个时候,毛主席是神一样的存在,知悉江青这样害毛主席,我们都气得不行,非常恨江青。在课间活动玩耍时,便在墙上画一个秃头女人像,把江青二字倒写,大家轮流用自制的弹弓瞄准射击。
那个时候,任何亵渎毛主席的话都是禁忌,在偏僻的山村小学,有特殊的禁忌方式。在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一个叫庄庄的同学在课外活动时说,毛主席晚上和江青一起睡觉哩,立即有人报告了班主任老师孙自忠。孙班主任在下午自习课上让庄庄同学在全班作检讨,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还有一次,杏树湾一个姓司的同学,因为爱放屁经常遭同学骂,一天下午自习课他又连续放屁,臭气熏得大家群起而攻之,各种脏话迭出。司同学愤怒了,也用脏话回击大家,并说,放屁咋了?毛主席也放屁呢!
此话一出,立即有人骂他反动,要报告老师。司同学脑子机灵,自知情急之下撞了大祸,慌忙赔情求饶,并用书包里的煮洋芋、糜面馍馍贿赂大家,还许诺第二天给大家带白面饼子。大家吃了煮洋芋和糜面馍馍之后,已经嘴软,又期待第二天的白面饼子,便饶了他沒有报告老师,他躲过了一劫。可是第二天的白面饼子带了没有,有几个人吃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位司同学人高马大,他一直自称会拳术,经常会伸胳膊踢腿给大家耍几路。他还能用拳头和掌在墙上、树上连续击打,手碰烂也一点都不在乎,他说这就叫功夫,天天练就能练成铁砂掌,把人的头和胸脯随便拍碎,他二爸已练了几十年,一拳能打折一棵大树。他们家祖传的这功夫,让大家一直有些害怕,这可能也是没有人把他的反动话报告老师的另一个原因吧。
在这个事情之前,还有一个晚上,家里来了亲戚,父亲陪亲戚在火炉旁熬罐罐茶,我爬在跟前就着油灯盏亮光看小人书,亲戚突然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随口说长大了当毛主席呢。结果亲戚噎住了,瞪大眼睛看着我,父亲大怒,骂我混帐、瓜怂,要撕烂我的嘴。此后,父亲唠唠叨叨地骂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当时,我常常会想,毛主席这么厉害,他一天会吃什么?肯定经常吃的是猪肉白面饼子和长面,可能还有仙草天鹅肉之类。一次和二哥一起吃高梁面馍馍,馍馍又硬又粗,实在难以下咽,我就问二哥,你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啥吗?二哥瞪了我一眼,好像很懂的样子,他说毛主席根本不吃高梁面,也不吃玉米面,人家吃的全是面精。我问面精是啥?二哥说你连这个也不知道,面精就是白面中最好的,加着糖精,甜得很!
(六)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似乎很快乐没有忧愁烦恼,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许多忧愁烦恼的事。
当时特别害怕劳动。到生产队劳动虽然累和苦,但劳动结束还能吃一顿饱饭,因此也有期待。比较害怕的是学校劳动。从四年级开始,每周固定有半天劳动课,有时候也会连续一天两天去生产队劳动。有一段时间,劳动课的内容是在学校后面的山上挖种树的台阶。这活儿,年龄大一些的同学还吃得消,可是像我这样当时十岁左右的孩子,拾麦穗拔杂草还凑合,抡镢头用铁锨则根本不行。但是必须热爱劳动,必须扛上铁锨上山,想请假开溜是不可能的。
劳动分成许多小组,一般是三个人一组,并分配了具体任务。和我一组的是贾牛儿和岳新林。
牛儿比我大一个月,劳动能力与我差不多,甚至还比我差,新林虽然才大我一岁多,却是劳动的一把好手。他干活一人能顶仨,在山坡上挖种树台阶时,镢头铁锨轮流进行,一会儿台阶就成型了,我和牛儿只是帮着平整一下堆积的土,然后挖种树的坑。新林抡起镢头挖山、拿起铁锹铲土的样子,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我们一起劳动时,他一直像大兄长一样关照我们,承包了我们所有的活,现在想起来还是感动不已!当时他自称老愚公,把我和牛儿叫愚公娃儿。
说起小学时的劳动,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四年级时,学生要给公路上铺砂子,从河湾里用铁锨捞出砂子,装到筐子里,两个人用一根长棍抬上,运送到指定的公路段落。我和牛儿、东平等四名同学抬了两趟后,饥饿困乏,实在抬不动了。走到一僻静路段,四顾无人,便将砂子倒在树下,然后直接回家。
我们的偷懒行为被发现了。
第二天下午,张发源老师召开全班会议,要我们检讨。我们四个人各写了一封检讨书,站起来胡乱念了,然后一直站到班会结束。本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张老师在班会结束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这种劳动态度对吗》。这事现在想来应该一笑置之,可是当时,在写作文时,羞愧耻辱之感陡生,特别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完作文题目时,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转向我们四个人,我脸红心跳,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那篇作文我具体写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自己骂自己,许多词语是从报纸上抄的,最后自己找的原因是这种劳动态度非常错误,是贪生怕死的逃跑行为,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而且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很大关系。
(七)
最怕的劳动是放学回家之后和星期日、寒暑假的拔猪草和拔柴禾。
夏天的时令长,下午放学后太阳还老高。一回到家,必须按照大人的指令,提着筐子给猪拔草。
这个时候,往往是几个小伙伴结伙钻进庄稼地里,边胡说乱吹边慢悠悠的拔草。筐子很快就装满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早点回家,因为回家早了又要被家长赶出来继续拔草。于是,有躺在庄稼地里的,有抓各种昆虫的,玩得不亦乐乎!看来,磨洋工这事,从小就在骨子里有,不需要别人教。一直等到天黑了,才提着一筐猪草懒洋洋的回家去。
猪吃的草就是庄稼地里的苦渠菜和灰菜,当时满庄稼地都是,生长得异常茂盛,拔回家后扔到猪圈里,猪便选择性地吃。最近几年这两样草很火,变成酒店里的上等菜,据说营养丰富,可降三高,价格不菲。有个段子,说是一个我们家乡的老板到南方去谈生意,南方老板点了一盘苦渠菜,菜上来后便特别介绍这个菜的价值功效,最后问你们那地方有这菜吗?家乡的老板说有,但我们那儿用这个喂猪。
星期日和寒暑假的劳动是拔柴禾。
那个时候没有煤和液化气,做饭、烧炕取暖全用树枝和柴禾,所以一有空闲时间到野外拔柴禾,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劳动任务。
经常一起结伙拔柴的有进儿、进辉、元元。我们每人扛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马家湾、灰灰咀、河那坡等地拔柴禾。我们那里的柴禾主要是蒿子、芦子和兵草,早早起床,满山遍野的寻找,到中午时分每人拔两捆柴禾,用棍子挑回家,下午亦然,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星期日和暑假几乎每天如此。寒假则是扫填炕,在地埂上、草地里,清扫一些腐烂、干燥的柴草,挑回家去用作烧炕的燃料。
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几个小伙伴每人背着小背篓,结伙去生产队的苜蓿地里捡拾苜蓿根。捡了大约有半背篓时,看护田地的人喊叫着追过来,吓得我们背上背篓就跑,跑了一段路,看护的人不追了,我们停止逃跑喘气,却发现元元小伙伴不见了,赶紧寻找,原来那家伙逃跑不及,急中生智,将背篓放在地埂下面,他爬在背篓后隐藏,看护的人只顾追赶前面逃跑的,反而遗漏了后面隐藏的。
(八)
那个时候,我是喜欢写作文的,除过上面提到的那篇命题作文。
那时候写作文,基本上是胡拉八扯,围绕题目乱拼凑。
我刚到四年级的时候,调来了一位姓王的校长,给我们教政治课。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刚来就让我写一篇发言稿,是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的。我东抄西抄,拼凑了一篇,现在能记得的内容,就是最后一句话:“这就是师道尊严的表现,我们要彻底批判。”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含义,在报纸上乱抄的。校长看了后,在最后又加了“肃清其流毒”几个字。我当时感到校长加上的这几个字很别扭,心里很不愿意,但又不敢说什么。过了几天开全校大会,兴高采烈地拿着稿子在发言台上念了。
不过,我当时抄文章的水平还算可以,能把报纸上的话稍微变一下,变成自己的话,并且和自己的环境结合起来。而那时写作文,许多学生就是直接抄,一字不改,抄够字数就完事。有一个叫江来子的同学,写作文时抄了一句“我代表中央委员会……”,被老师在全班嘲讽批评,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中央委员”,我的内心便一直瞧不起他。
校长还给我布置过一篇发言稿,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校长看了后把我叫去,他说你的这句话缺了内容,要补齐。我恭敬地问缺了什么?他让我自己去查。可是我怎么也查不出,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在我一筹莫展之时,“中央委员”拿了一份报纸给我,我才知道标准答案是“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赶紧填充完整,从此再也不敢看不起“中央委员”了!
五年级时写过批邓的发言稿,具体内容完全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经常用的词语是,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时候,学校经常召开全校大会,学生带着凳子按班级排序坐在学校院子里,前面摆几张桌子,校长和几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每个年级有一名学生代表发言,都是在报纸上抄下来的话。开会之前各班统一唱歌,歌声此起彼伏,开会中途大家还要举起拳头喊口号。
因为批邓,我的一个堂哥改了名字。他本来叫张小平,可是开始批邓后大家都喊他邓小平,他便改名为张有良。这位改名的堂哥,以后考取了医学院,现在也是专家一级的人物了。
(九)
那时候公社和大队的大会比学校更多,学生们要经常参加,大多数是批判会,有时候是忆苦思甜会。
忆苦思甜经常有老贫农雇农讲解放前的苦。有一个表叔,按乡俗我叫他姑舅爸,他讲的很有名,一次在学校讲时,说他们给贾家干活,干活的人吃的是箩儿下面的,贾家吃的是箩儿上面的。
贾家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大地主。
又说给贾家干活时虽然苦,但能吃饱,主要是六O年把人饿得劲大了……
在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上,往往在宣布会议开始时,公社或者大队的干部会大喊一声“把四类分子押上来”,于是就有背枪的民兵和手持红缨枪的红小兵,押着七老八十的几个四类分子到会场,面朝开会的人一字排开站着。
我那个时候最希望干的事是持红缨枪押四类分子。
我发现拿红缨枪的有个叫永良子的红小兵,拿枪的姿势和电影上的不一样,站立和走路的动作一点也不威武,心里就很不平衡,为什么他能押人我不能?
有一次课外活动时,我在操场看见张发源老师,就跑过去要求:“老师,以后红小兵押四类分子,把永良子换成我能行吗?永良子拿红缨枪的动作不正确,我能像潘冬子那样拿红缨枪。”
张老师看着我哈哈大笑,把我的话告诉了旁边的其他老师,他们都一齐大笑起来。然后,张老师笑着说,你的个头太小了,不能押四类分子。
于是我就非常郁闷!此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个子小有什么不便,这时立刻感受到一种自卑!
(十)
那个时候,在参加各类劳动的同时,学生们还要排练节目去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水利工程建设工地慰问干活的贫下中农。
我至今还记得校长带着我们去慰问的情景。戴眼镜的王校长,捧着一张大红纸,用普通话宣读慰问信,我们在后面偷偷地笑,念完慰问信之后就表演节目。
这位王校长,因为经常用普通话念慰问信,学生们在背后给他起了外号叫“王料片”。
我们演的节目有舞蹈,还有眉户剧。
记得我参与的舞蹈有《北京的金山上》《献给亲人解放军》,四名男生四名女生,是藏族舞。我穿的是大哥当兵复员时带回来的一件崭新的绿军上衣,又宽又长,好像是风衣,只穿一只袖子,腰里扎一根长长的象围巾一样的带子,另一只袖子垂在背部,这种打扮当时感觉很酷。
演过一出眉户剧,我们三男三女六个人,扮的是三个老汉三个老婆子,天还没有亮就赶往生产队的工地上干活,走在路上六个人先后相遇,相互戏谑打闹。我演的是老汉里面的老大姚木匠,第一个出场,刚出场的台词是:雄鸡刚叫第一声,老汉我赶忙就出工,别看老汉年龄大,样样活儿落不下。
孙思明老师还给我们排练过一出眉户剧,是一男一女两夫妻给生产队喂猪的戏,让我演剧中的男角,台词都记下了,可是女角是我的一个堂姐,在戏中男的要叫女的“老婆”,于是我就坚决不演男角了,孙老师对我软硬兼施,均无效,最后我挨了老师一顿打才作罢,男角换了人。
(十一)
在学黄帅反潮流批邓的前后,还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学生写作文必须要和投降派挂上钩,比如前面劳动中的偷懒行为,我们都归结到投降主义。当时,对于“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这句话根本理解不了,一直很纳闷,既然投降这么好,为什么要批判呀?但是只能在心里想,根本不敢公开说,在公开场合,还要假装很懂的样子。不过,对于伟人评水浒的那段话,却背诵得滚瓜烂熟,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
写过好几篇批判宋江投降派的作文和周记,现在一个字也不记得了。但是,因为批判宋江,反而引发了了解水浒的各种想法,当时学生中私下偷偷传看水浒的小人书,是32开大小发黄的旧纸,纸质很厚,人物肖像画得很逼真很好看,直到今日,《石碣村》中宋江和晁盖的画像仍然历历在目。我看过的小人书,除了《石碣村》之外,还有《杨志卖刀》《大闹五台山》《林冲雪夜上梁山》《三山聚义》《三打祝家庄》《醉打蒋门神》等。
看了水浒小人书之后,彻底激发了我读小说的兴趣,当时新版的《水浒传》公开发行,我读了一百回的那种版本,半懂半不懂,很是着迷。读水浒之外,还读了三国、西游、说唐,不知哪位同学从家里偷拿了竖排繁体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说唐全传》,书的前面都有主要人物的画像,喜欢看书的学生便悄悄用馍馍、杏、梨、甜瓜等食物交换阅读。
当时我对繁体字大多不认识,阅读的时候便问父亲,如果父亲也不认识,就自己瞎蒙。那个时候没有字典,我是直到初中二年级才买了一本《中国汉语小字典》,至今还保存着。
我最喜欢读的是《说唐全传》,对十八条好汉极为着迷,常常给玩伴讲秦琼、罗成、李元霸。言谈举止也受水浒和三国的影响,放学之后,手中要拿一根长杆子挥舞,玩伴之间见面,也要相互抱拳问候,常用语是“敢问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还相互起了外号。
在读历史小说的同时,还读过一本半文言的小说《金镯玉环记》,内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与一位书生的爱情历程,几经磨难终成眷属。长大后一直记起这本书,想要再读,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十二)
模仿水浒、三国和电影里的情节打架,是小学时光的重要内容。
在四年级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七、八个经常一起玩的小伙伴,相聚在一个周围长满柳树椿树的大坑里,那个坑是以前修房取土时挖的,废弃多年,坑里杂草丛生,又长出了一些小树。我们清除了杂草,用小铲子挖了两排台阶,铲成十几把椅子的样子,像梁山泊好汉那样排座次,记得我坐了第三把交椅。
于是,每天放学后,或者到了星期日,我们就要到那个坑里自己的座椅上坐好长时间。第一次进行排座次的玩伴有五、六个人,是军魁、进辉、象魁、元元等,以后改军和引旦儿也入伙。
过了一段时间,其他人都不来了,我和改军、引旦儿三人还是坚持了好长时间。同时,我们三人还学桃园三结义,搞了结拜仪式。
结伙打架一直是那时候乐此不疲的项目,有时候是做游戏假打,分成两队摆开阵势,两队各出一人在阵前打斗,或者是空手摔跤格斗,或者各拿一根长棍乱打一气;但有时候打架是真打,一般是两个村庄的学生结伙打斗,除了偶尔拿着棍棒追逐较量外,大多数的时候是土块战,我们叫“打胡基仗”,即一方埋伏在墙角、地埂或者小树林等隐蔽处,等另一方经过时,便突然袭击集中投掷土块进行攻击,在对方逃跑时,埋伏的一方呐喊着追击,一直到把对方打得四散逃走才作罢。
为了便于埋伏打仗,我们还在土堡子的墙头用大土块堆积砌垒成碉堡状,留有观望口,捡拾上许多小土块堆放在旁边,等到其他村的学生路过时,向他们投掷土块,还用自制的望远镜装模作样的观察“敌情”。有一次我们攻击秦王村的“敌人”时,被人家集中反击,攻打到土堡子上面,我们落荒而逃,辛辛苦苦修建的碉堡被捣毁。
(十三)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篮球。
当时的篮球活动很多。一到春夏季,小学的操场里几乎每天都有球赛,常常是我们村上的篮球队与机关单位的联队比赛,五一、六一、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里,有全公社的比赛。每当听到哨声,我的神经立即兴奋起来,不顾一切跑到操场看球。
篮球场上最耀眼的明星是孙思明老师,他跳的太高了,冲篮时能摸到篮筐,远投又很准,他投篮的动作一直是我模仿的对象。还有我们村的祥子,简直是神投手,常常一过中线,就双手把球高高举起抛出,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落进篮筐,只听到网子唰的一声响!
当时学校只有一大一小两个篮球,在课外活动和体育课时,我们能摸一下小篮球,那是用橡皮做的,很光滑。放学后或者星期日,就只能玩“毛蛋”。毛蛋是用烂棉花或者棉羊毛裹着一块橡皮用绳子包扎成篮球的样子,弹性当然不如篮球,但玩起来与篮球差不多。经常会有人吆喝一声“打毛蛋走”,大家便蜂拥而去操场里打毛蛋玩。
学校里各班之间经常进行篮球比赛,一、二、三年级一个组,四、五年级一个组。我一直渴望自己是班队的一员,但是个子太小,一直没有资格,曾向老师要求过进班队,但是老师一直说我没力气,不行。三年级时,有一段时间被选到班级篮球二队,但是根本上不了场,打不上球,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也喜欢乒乓球。进不了篮球队,我就刻苦练习乒乓球,到四年级时,乒乓球技术在学生中已经是高水平了,到了五年级,还在全校学生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冠军。奖品是一张画,画面是一个老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妇女挎着菜篮子,提着鲤鱼和什么食品,拖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周围开满鲜花。这张画母亲一直贴在西房的墙上,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存在。
那场冠亚赛在我和李东魁之间进行,我3:1战胜了他。那次比赛在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当时乒乓球水平较高的有东平、来柱子、李东魁,他们都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得了冠军后,我骄傲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和永升老师较量了,结果有一次和永升老师打了五盘,全部败北,每盘连10分都没有突破,记得永升老师鄙夷地说,你还差得远着呢。
除了篮球、乒乓球之外,经常玩的运动还有滚铁环、踢毽子、跳房等。我的滚铁环技术也很不错,经常和自愿子一起玩,我俩水平不相上下。
(十四)
对于小学时光的记忆,有些是断断续续的,尤其是三年级之前的事,记忆很不完整,这大概与我在二、三年级时经常发作的头痛疾病有关吧。
从二年级开始,如果是晴天,每天早晨在太阳出来时,我的头便炸裂般疼痛,只要一看见太阳光,头脑里便“嗡”的一声响,立即疼得爬在课桌上,眼冒金星,恶心呕吐。这般时候,会有同学扶着我走出教室,我在教室外歇缓一阵之后,就一个人摇摇晃晃走回家去睡觉了。而在中午饭吃过之后,又会奇迹般的痊愈。为此,母亲曾好多次带我到公社卫生院,吃药、扎针灸治疗,但效果不行。
所以在二年级、三年级时,我最怕的是早晨的太阳,而阴天、雨天则平安无事。这样折腾了快两年,在三年级升级时,父亲和老师商量让我留了级,我在小学读了两个三年级。
在第二个三年级时,头疼病突然好了,此后三年多没有发作,直到初中一年级时又发作,这是后话。
在第二个三年级,我迷上了写字,钢笔字写的横平竖直、整洁有序,做的作业经常受老师表扬。当时我们班上字写得好看的还有一个叫进辉,按辈分是我的侄子。我俩被老师命名为“第一写家”和“第二写家”。曾经抄写过几页字,老师交到县上参加书法竞赛,可是交卷后再无下文,估计我们当时的字在全县范围内还是上不了台面的。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培训班,看到老师的板书或者笔记,然后凭记忆埋头即兴练一下,从来没有刻意练过,也没有请教过老师字应该怎么写。记得曾看到过张发源老师写的隶书,回家后便把“语文笔记”重抄了一遍,模仿的是张老师的隶书,把笔记交给班主任孙自忠老师批阅时,他竟然不相信是我写的,查问了好长时间,最后我要当场书写验证时,他才作罢。
(十五)
那时候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总是感觉一年特别长。毛主席逝世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便临近尾声,我们准备升初中。
此前小学升初中已经多年不考试了,突然传言要进行升学考试,大家都有点紧张。可是最后却没有考试,只根据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确定了是否上初中,我的成绩除数学刚刚及格外,其它课的成绩都是90多分,升学没有问题。
中学派了孙建白老师到我们班上和全体学生见了一面,其实就是点了一次名,他拿着学校毕业考试的成绩单,让点到名的学生站起来他认一下,就算是完成了升学考试。孙建白老师满头银发,笑容可掬,梳着整齐的大背头,穿一身灰白色的中山装,笔挺整洁,风度不凡。他本来是安徽一个大学的教授,被打成右倾后发配到甘肃,之后又被下派到县城,然后再被下放到我们公社的中学。他儿子叫孙小白,小我两岁,当时也在我们小学读书,我们常常一起玩。我升初中后,孙建白老师还教过我数学和生物,两年后他们全家搬走了。据传他和华国锋主席认识,被调到北京或者调回安徽去了。
(十六)
小学六年,我一直不是很安分。
嗓门大,爱争吵,和同学吵架不服输,非要赢不可。每当吵起来,便一定要在音量上、语言上胜过对方才罢休。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老师在通家书缺点一栏里对我的评语是“爱骂人!”我看到后羞愧万分,找到老师要求修改,被老师骂走,于是便把通家书装在身上不敢示人,回家后对父亲说今年没有发通家书。
个子小,体力不行,却经常和人打架。记得在一年级时我不满六岁,和大我两岁的一个同学在河里抬水时,我们发生争执相互撕打,被人家用水瓢打落了我的两颗门牙,幸亏那时候到了换牙的年龄,没有落下后遗症,以后与同龄的、比我大的学生又多次打过。那个时候,小孩子打架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人找家长,也没有人要求赔偿,我的牙被打落,一个月后父亲才知道,他竟然没有一点心疼,只说娃娃家人不要紧,以后就长出来了。果然,三个月后长出了新牙!
五年级时和同桌叫霞霞的女生也经常打架。那个时候男女生的界限已经开始严格了,只要霞霞无意中碰我一下,或者她的书本越过桌子的中间线,我就手痒痒想打她一下,或者捣两拳,或者踢两脚。霞霞的性格也极为刚烈,只要我打她,她肯定会还击,所以我也挨了她的许多拳脚,有一次她还把我小胳膊抠烂了。而有意思的是,当过了十几年我结婚之后,竟然发现霞霞是我妻子的小姨。前几年我和妻子见到这位同桌小姨时,共同回首当年打架的情形,不禁感慨人生的无常与奇妙!
是啊!世事无常。
六年的小学时光,在人生的旅途中是短暂的,转瞬即逝。那些苍凉的扉页,当我们去回首之时,有时会感觉那段时光纯粹是一场空。但是,当我们细细的回忆、品味之时,又感觉到它的漫长甚至停滞!
快乐当然是主旋律,一点小事就能激发快乐,所以小学时光总体是快乐的。好动的我,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兴奋,想起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夸赞,会一个人情不自禁的笑出声来;想起母亲要做好吃的,会兴奋得手舞足蹈,迫不及待;在去看球赛或者看戏看电影的路上,也会兴奋得大喊大叫……
但是,在快乐之外,小学时光的漫长,总是与两个字联系起来——饥饿。
小学六年深刻地感知了饥饿的滋味!
学生们攒到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吃。那个时候,一年里能吃上白面的时候屈指可数,面条、油饼是绝对的奢侈品,只有在春节时才能见到。长年累月的粗粮,高粱面、玉米面、洋芋、萝卜以及各种野菜,吃的人既胃里反酸,又饥饿难耐。
班里常常会发生偷馍馍事件,每次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自己带的馍馍被偷之时,大家都非常害怕,怕追查到自己的头上。有的老师往往虚张声势地追查一下,不了了之。而有的老师则以哪位同学的脸红作为判断标准,盯着大家看,这个时候,常常是老师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一咋唬,就有同学站出来投案自首。
这就麻烦了!
这个时候往往要开班会,偷吃的同学要当众作检讨,自己辱骂自己,而偷吃的原因都会归结为好吃懒做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那个时候,父母一直告诫我,千万不要偷吃东西。
除此之外,还会莫名其妙的恐惧、失落,害怕一切已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灾难,怕地震、怕大雨、怕山塌下来,还特别害怕鬼。走到僻静的地方,最害怕突然窜出一个鬼来。我最怕有鬼的地方是村子里的梨树园子和核桃树园子,每次一个人走到这两处地方,浑身会立刻起鸡皮疙瘩。
俱往矣!
小学时的各种情景,各种情绪,虽然尘封几十年,但是一旦回首,仍然感受到岁月静好!那有笑有闹有哭有荒唐的年龄,那饥饿的年代,那些经历过的春夏秋冬四季以及阴天晴天雨天雪天,那些一起玩过的小伙伴……那所有的一切,既平淡无奇又不乏精彩,既恍若隔世又恍如昨日,这,就是人生吧!
注:作者丨张正伟
编辑丨张海冬
图片:来源网络
欢迎扫码